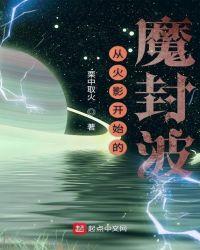笔趣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63章两个老不死的(第1页)
第663章两个老不死的(第1页)
开车回了城里,两人没回家,而是直奔厂房。
这次谈成了合作,要提前备货,张小麦得回去安排。
刚进了厂房,就听见里头吵吵嚷嚷的。
几个工人聚在门口,看样子是有人闹事。
江舒棠皱眉,下车后便赶忙小跑着过去。
大家看见江舒棠回来,都围了上来。
“江厂长,您可算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江舒棠皱眉问道。
一个女工人凑了过来,压低声音说道:“老板,是杏花的父母过来了,在咱们厂里闹了两天了。”
张小麦这会儿也赶了过来。
夜色再度降临,老宅的厨房却亮着灯。男孩守在灶台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锅里翻滚的汤汁。火苗温柔地舔舐着铜锅底,发出细微的噼啪声,像某种古老的低语。少女坐在门槛上,膝上摊开一本泛黄的食谱,纸页边缘已磨损起毛,字迹是苏晚亲笔所写,墨色深浅不一,仿佛随时会随风散去。
“收汁要慢。”她轻声道,“急不得。就像等一个人回头看你一眼,快了,味道就跑了。”
男孩点点头,用木勺轻轻搅动。他的手仍有些抖,但眼神已不再慌乱。那口焦掉的红烧肉被他主动倒进垃圾桶,连同羞愧一起埋葬。现在这锅,是他重新开始的承诺。
窗外,槐树静默如守夜人。一片花瓣悄然飘落,贴在窗玻璃上,金光微闪,浮现三字:“再等等。”
时间在香气中拉长。当最后一滴酱汁裹住肉块,油亮如琥珀时,男孩终于关火。他小心翼翼揭开锅盖,蒸汽扑面而来,在空中勾勒出一个模糊的人影??短发,围裙,手里握着锅铲,嘴角含笑。
“苏……苏老师?”男孩脱口而出。
人影未答,只轻轻点头,随即消散于风中。
少女起身,取来青瓷碗,盛了一小块肉递给他:“尝尝。”
男孩咬下一口,眼睛猛地睁大。不是因为多美味,而是那一瞬间,他脑中浮现出从未见过的画面:一个小女孩蹲在巷口啃冷馒头,衣衫破旧;一位女人走过来,蹲下身,递上一碗热腾腾的红烧肉;小女孩抬头,眼里有泪光,然后笑了。
“那是……我奶奶?”男孩喃喃。
少女微笑:“心音不止传味,也传记忆。有些人一辈子没吃过苏晚做的饭,却因这一口,记起了被爱的感觉。”
话音刚落,院外传来脚步声。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杖缓缓走来,白发苍苍,眼角刻满岁月沟壑。她站在门口,望着厨房里的灯光,嘴唇微微颤抖。
“奶……奶奶?”男孩惊叫着跑出去。
老人一把抱住他,眼泪簌簌落下:“我找了你七天……你说要去学做饭,我就知道,一定是来了这里。”
原来男孩家住城郊棚户区,母亲早逝,父亲酗酒,奶奶靠捡废品养他。那天他在垃圾堆旁看到一张宣传单,上面画着心音亭,写着:“只要你愿意,就能学会让人幸福的味道。”他攥着纸条走了二十里路,鞋都磨破了。
少女端出一碗红烧肉递给老人。老人接过,颤巍巍夹起一块送入口中。刹那间,她身体一震,眼眶骤然湿润。
她看见年轻时的自己,坐在乡下土炕上,丈夫端来一盘红烧肉,笑着说:“你嫁给我,以后顿顿有肉吃。”那是他们婚后第一顿饭,也是最后一顿??三天后,丈夫在工地事故中离世。
“原来……”老人哽咽,“这味道,是他说过的‘家’。”
那一夜,祖孙二人留在老宅歇息。男孩睡在念恩曾住的小屋里,枕边放着那口铜铃。半夜醒来,他发现铃身微温,仿佛有人刚刚抚摸过。他轻轻摇了一下,声音极轻,却引得院中槐花轻轻晃动。
次日清晨,少女带他们参观心音传承所。这里原是萧家废弃的祠堂,如今改造成教学空间。墙上挂着百张照片:有盲人厨师在助手引导下切姜片,有自闭症少年为同学盛饭,还有外国留学生跪在灶前磕头拜师。
“我们不收学费。”少女说,“只收一颗想让别人吃得开心的心。”
中午,传承所开课。三十多名学员围坐厨房,男女老少皆有。主讲是一位中年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厨师服,胸前别着一枚铜制徽章??那是首批“心音认证厨师”的标志。
“我是李志国。”他开口,声音沙哑,“十年前,我杀了人。”
众人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