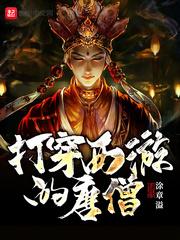笔趣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69章被耍了(第2页)
第669章被耍了(第2页)
第七天,艾力提出要试做烤包子。难点在于面皮擀薄、馅料调味、炉温掌控。林溪特地请镇上铁匠重修了土馕坑,又让人从新疆寄来正宗的胡麻油和野韭菜。
他揉面时格外专注。手背青筋凸起,汗水顺着鬓角滑落。他一边揉一边念叨:“她说面要三醒三揉,像人心,揉多了硬,揉少了散。”
馅料调好后,他试着包第一个。动作生涩,收口不严,露了馅。第二个稍好,第三个竟有了弧度优美的褶子。第十个时,已能稳稳托在掌心,像个小小的月亮。
入炉前,林溪问他:“想好怎么烤了吗?”
“火不能大,也不能小。”艾力说,“太大,外焦里生;太小,没了灵魂。我妈说过,最好的烤包子,是外皮裂一道缝,热气慢慢冒出来,香味一点点散开,像人在笑。”
林溪点头,亲自点火。
四十分钟后,第一批出炉。外皮金黄微裂,咬开热气腾腾,肉汁饱满却不腻,野韭菜的清香与胡麻油的醇厚交织。小芸闻到香味跑来,摸了一个,惊喜道:“陈叔叔,这个好像会发光!”
艾力笑了:“它不是发光,是心里有太阳。”
分享会上,艾力讲述了他妻子的故事。他说她本是县中学音乐老师,失明后仍坚持教孩子们唱歌。她说:“眼睛看不见,但声音能长翅膀。”直到病重卧床,她还在哼儿歌哄女儿入睡。
“她走后,我烧了她的琴,觉得活着没意思。可有一天,女儿偷偷打开录音机,放她录的歌。我听着听着,突然明白??她没走,她在声音里活着。就像现在,我在味道里,让她回来。”
全场寂静。连风都停了。
林溪宣布,艾力将成为“心音厨房”首位跨省教学志愿者,负责培训西北地区盲人烹饪讲师。合同签完那天,他独自在厨房待到深夜,一遍遍练习包包子,直到每一个都完美如初。
八月初,林溪帮他寄出一个包裹:十只真空密封的烤包子、一小罐玫瑰花酱、一碗冻好的奶皮子,还有一封信,是他一字一句口述,陈默代笔写的:
>“亲爱的古丽娜:
>
>爸爸学会了做饭。这次不是糊的,也不是咸的。是妈妈的味道。
>
>下个月,我就回家。咱们一起过生日,好不好?
>
>爱你的爸爸”
信纸折成一只小鸟,夹在罐子缝隙里。
送走艾力那天,暴雨突至。雷声滚滚,闪电划破天际。老宅的电路跳闸,一片漆黑。众人正慌乱找蜡烛,忽听得厨房传来轻微响动。
是陈默。
他在黑暗中点燃了煤油炉,架上铁锅,开始煮面。火光摇曳,映着他半边脸庞,沉静如古佛。
“别怕。”他对吓哭的小芸说,“你看,火还在。只要灶不灭,家就不散。”
那一晚,十七个人围坐在厨房,吃着最简单的清汤面,却吃得比任何宴席都庄重。面条入口温软,像一条通往过去的路,又像一根系住未来的线。
雨停后,林溪爬上屋顶检修电路。她看见远处山梁上,一道彩虹横跨沟壑,宛如桥。她忽然想起苏晚临终前说的话:“溪儿,人这一生,不是要活得完美,而是要活得有回音。”
她低头望向院子,陈默正在教新来的学员辨油温。他把手悬在锅上方,轻声说:“感觉那股热气,像不像春天的第一缕风?”
学员点头,眼里闪着光。
林溪回到厨房,在《心音笔记》写下新的一页:
**艾力?阿不都,2026年夏入学**
**课程完成:为女儿复刻亡妻的味道**
**当前课题:让爱穿越千里**
她合上本子,轻轻吹熄蜡烛。暮色四合,槐花落尽,新叶葱茏。
夜里,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垠麦田中,风吹麦浪,如海起伏。远处炊烟袅袅,有人在喊她吃饭。她循声而去,看见苏晚站在灶前,笑着搅动一锅粥;陈秀兰坐在廊下剥豆角;艾力牵着女儿的手,教她摸土豆的坑洼;小芸趴在案板上,用面粉写字:“我长大了要做厨师妈妈。”
而陈默,正端着一碗面走向轮椅上的母亲,口中轻唤:“妈,趁热吃。”
她醒来时,天刚微亮。灶膛余温尚存,铜铃轻响,似有若无。
她起身添柴,火苗“轰”地窜起,照亮整间厨房。
“来,”她对着空屋说,“吃饭了。”
屋外,晨雾未散,新的一天正从灶火中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