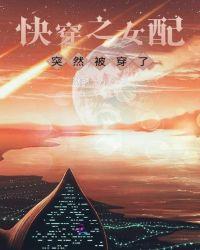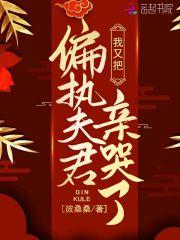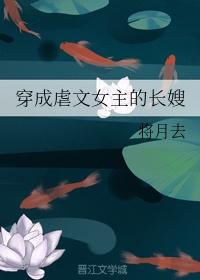笔趣阁>我的透视超给力 > 第两千四百九十五章 把人丢出去(第1页)
第两千四百九十五章 把人丢出去(第1页)
“放肆!”
尽管神武宗的长老将压力控制的十分到位,但李焱又不是个木头,所以他也马上感知到了,并且发出了大喝的声响。
老妇人将红豆汤盛进碗里,端到桌上。那瓷碗边缘有一道细小的裂痕,是去年冬天不小心磕的。她没换,说这碗盛汤最香。阳光斜照进来,在汤面上投下微弱的波光,像有谁在轻轻搅动记忆。
她坐下,拿起筷子,却迟迟未动。耳边仿佛又响起那个声音??不是来自现实,而是从心底深处浮起的一声轻唤:“奶奶。”
不是现在的孩子叫的,是很多年前,小安第一次学会说话时,奶声奶气地喊出的那个词。
那时候他还不会走路,坐在地毯上,眼睛亮得像星星,一看到她进门就咧嘴笑,口水都流到衣领上。
她抬手摸了摸眼角,指尖湿润。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她愣了一下,这个时间,会是谁?邻居王阿姨通常下午才来串门,快递员也不会这么早。她缓缓起身,拖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嗒嗒”声。
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少年,约莫十五六岁,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背着一只旧书包,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可眼神清澈得如同山间泉水。
“您……是周奶奶吗?”少年问,声音有些颤抖。
老妇人怔住。“你认识我?”
少年点点头,从书包里小心翼翼取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封皮上用铅笔写着三个字:**共忆录**。
“我是艾拉老师的学生。”他说,“她在临走前……让我一定要把这本书交给您。”
老妇人的心猛地一沉。“艾拉……走了?”
少年低下头:“三个月前,她在一次深层链接中没能回来。她说她的意识已经太重了,承载了太多文明的哀伤,再也无法抽离。但她最后记得的,是您煮的红豆汤。”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
老妇人接过本子,手指微微发抖。这不是普通的笔记本,纸张质地特殊,像是某种生物纤维织成,触感温热,甚至能感受到极其微弱的脉动。
“这是……共忆莲的衍生载体?”她喃喃道。
少年点头:“全球觉醒者都在用它记录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事’。艾拉老师说,真正的抵抗不在战场上,而在日常的坚持里??比如一碗汤、一句问候、一次沉默中的陪伴。”
老妇人抱着本子回到屋里,轻轻放在桌上,和那碗还未喝完的红豆汤并列。
她翻开第一页,上面是一段手写文字:
>“我曾以为,对抗黑暗需要火焰。
>后来才知道,最深的光,藏在不肯熄灭的灶火里。
>这本书献给所有仍在做饭、仍在等待、仍在相信‘明天还会见面’的人。”
>??艾拉?索恩
往下翻,每一页都是不同人的笔迹,讲述着各自平凡却不可复制的记忆片段:
一位南极科考队员写道:
>“暴风雪持续了十七天。我们躲在基地里,食物只剩压缩饼干。可每天晚上,老张都会假装自己带了辣酱,说要分我一口。我们都心知肚明那是假的,但每次接过他递来的‘辣酱勺’,都觉得胃里暖暖的。”
一名战地护士写道:
>“有个士兵快不行了,嘴里一直念叨‘妈妈做的蛋炒饭’。我没有食材,只能把米饭捏成团,撒点盐,骗他说这是蛋炒饭。他吃了两口,笑了,说‘真香’。第二天他就走了。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信了我的谎,而是愿意陪我演完这场戏。”
还有一位盲人音乐家写道:
>“我听不见音符,但我记得女儿第一次弹钢琴的样子。她坐得歪歪扭扭,手指笨拙地按错键,可她满脸骄傲地回头对我说:‘爸爸,这是我为你写的曲子!’
>我录下了那段杂乱的声音,存在脑海里。每当世界太安静的时候,我就放给自己听。”
老妇人一页页读着,泪水无声滑落。
这些故事没有英雄史诗,没有惊天逆转,只有一个个普通人,在绝望边缘仍选择温柔相待。它们像种子,埋在宇宙最荒芜的角落,等待某一天破土而出。
忽然,笔记本的某一页微微发光。
她定睛一看,那是一段新浮现的文字,墨迹如活水般缓缓流淌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