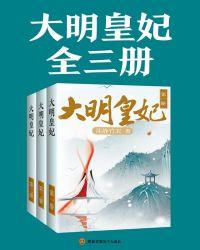笔趣阁>秉刀照雪(探案) > 问话(第2页)
问话(第2页)
父母打骂了他数回,也不见得能让他的目光自学堂离开半寸,回到脚下的泥地里。
本以为这辈子只能庸庸碌碌下去,不曾想天不负他,老宅旁的空屋子搬来了新友邻,是个念过书的老先生。
靠着老先生肚子里的三钱文墨,杜悯开了蒙,初识了混沌天地。
好在天道酬勤,元顺七年,杜悯成为了八百名庶人子弟中的佼佼者,考入四门学。
“我以为我能就此入仕,哪怕是回沧南道,做个普通县官,”话及此处,杜悯自嘲一笑,“大人可见过那些世家子弟是如何搓磨人的?”
假期在时,那些官宦子弟纵马斗蛐蛐,回了国子监,便拿人来取乐。
首当其冲的便是四门学、书学与算学的弟子,只因入学这三门的平民学子最多。
杜悯道:“那时候死上个把人也不足为奇,天下百姓但凡有些学识的,谁不想削尖了脑袋挤进来?可这地界对我等只是炼狱,刀山火海也不见得更难熬!”
心绪翻涌之时,杜悯握着铁链狠狠一挣,却挣不开这命。
他说:“口头折辱是家常便饭,拳打脚踢也并未少见,可笑我因课业上多得了助教一句称赞,从此便再无宁日。”
元行微听了沉默半晌,或许是想到元行煦还在国子监念书,她多少有些心中不忍:“连师长也无动于衷吗?”
杜悯摇了摇头:“司业为保官途从来不管,有几位博士、助教倒是提过几次,可过不了多久,便不能来上课了。”
难怪陛下要都察院也入局。
元行微心下一凛,这样的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或许时至今日亦未断绝。
“剽窃是怎么一回事?”岑阙问。
杜悯垂下头,压抑下数年来的苦闷:“我向来不忿此劫——他们打不服我,也只当我是个不受驯的野马,日后待我离京上任,便再也见不到面了。可时也命也,竟让我搭上了东宫的船。”
东宫,废太子。
事涉前朝,元行微与岑阙皆是面色一变。
周围人也深知不该多听,鞫讯郎官与照衣、兰钦先后出了诏狱,冷瓦廊下,一时间只剩了元、岑二人在听。
杜悯继续道:“我当时作《田间除害论》,要清蠹虫,还大岳朗朗乾坤,入了先太子的眼。元顺十三年夏,太子詹事府少尹欲举荐我入仕,我便将此事作为投名状,请先太子率先清查国子监。剽窃丑闻,便是那时候传出的。”
人证物证确凿,多方重压之下,一个小小的庶人杜悯根本翻不起浪。
元行微那时还未出生,不大清楚旧人旧事。
她问:“废太子不曾为你转圜?”
岑阙闻言,稍稍贴近了她,低声道:“那时候东宫有喜,想来分身乏术。那人本就因谋逆被废,说不准是将杜悯杀鸡儆猴的。”
“至少先太子有意清查!”杜悯愤然道,“否则将我这条命拿去便是,何须令邓少尹给我这文心画斋的地契与铺面!”
意外得知文心画斋来历,元行微略有些诧异。
她沉吟片刻,“你与展画屏相差二十余岁,又是如何认识的?”
不料杜悯冷嗤一声:“如何认识……同病相怜之人,还能如何认识?展画屏也不过是可怜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