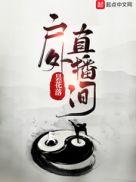笔趣阁>没钱怎么当明星 > 第二百七十一章 焚书意何严通书词何婉二合一(第3页)
第二百七十一章 焚书意何严通书词何婉二合一(第3页)
台下一片寂静。
“技术主权,就是新时代的国家安全。”他继续说道,“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保卫战中最年轻的战士。”
讲座结束后的自由交流时间,一个瘦小的男孩怯生生递上一本手工装订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竟是用铅笔绘制的一张芯片结构图,旁边密密麻麻写着注释。
“这是我设计的‘萤火芯2号’改进方案。”男孩低声说,“我觉得可以在电源管理模块加一层动态调频机制,这样太阳能供电的设备就能撑得更久。”
王曜仔细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抬头问:“你几年级?”
“初一。”
他笑了,拍拍男孩肩膀:“下周来深圳,住我们公司宿舍,跟研发组一起做仿真测试。”
男孩瞪大眼睛,几乎不敢相信。
临别时,阿英赶来送行。她穿着校服,扎着马尾辫,笑容灿烂如春阳。
“王叔叔,我高考想报计算机专业。”她说,“我想回来,建一座属于大山的科技馆。”
王曜郑重点头:“等你。”
回到深圳当晚,林浅带来一个惊人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萤火芯”项目收录进“全球开放硬件典范案例”,并提议在全球设立五个“开源芯片协作中心”。
“我们赢了。”她说。
王曜却只是默默打开电脑,进入内部监控面板。
全球设备在线数:**58,321,9**
新增用户画像中,60%来自年收入低于3万元的家庭;45%的活跃设备运行在无稳定网络环境中;平均每台设备日均调用AI服务超过120次。
这些数字不像胜利,更像责任。
几天后,他在清华授课时被学生提问:“王老师,你觉得星火最终能做到多大?”
他沉默片刻,反问:“你们知道张维清老先生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无人作答。
“他说:‘只要还有人在写代码,希望就不会死。’”王曜望着窗外飘起的细雨,“所以我不关心它能做多大,我只在乎,它能不能一直守护那些最需要它的人。”
课后,一位研究生追出来,递给他一份研究报告。
标题是:《基于星火OS的农村慢性病预警模型可行性分析》。
作者署名:**王小禾**。
王曜怔住。
那是他十年前在腾讯带过的实习生,后来因家庭变故辍学返乡,从此杳无音信。
报告末尾写着:
>“我在老家卫生院当护士。看到你们做的系统,我想试试能不能帮乡亲们早点发现高血压和糖尿病。虽然我不是程序员了,但我还记得您说过的一句话:‘每个功能背后,都应该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
王曜当场拨通电话。
接通那一刻,他听见背景里有婴儿啼哭和老人咳嗽声。
“小禾,”他声音沙哑,“回来吧。我们一起,把这条路走得更远。”
春天悄然过去,夏日来临。
六月,首颗搭载“萤火芯”的试验卫星由长征六号发射升空,成功实现太空边缘计算;
七月,全国首个“无障碍智慧社区”在杭州落地,盲人可通过语音导航独立出行;
八月,星火OS正式进入非洲市场,首批十万台教育平板运抵肯尼亚,配备斯瓦希里语语音包;
九月,国际电信联盟宣布采纳“星链协议”作为跨设备身份认证参考标准之一。
而在这所有的辉煌之下,最让王曜动容的,是一封来自西藏边境小学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