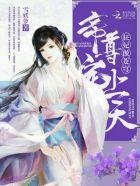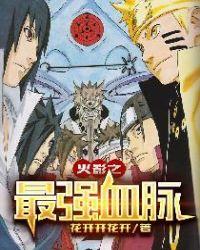笔趣阁>全家夺我军功,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 第680章 争权逼皇上赏赐(第2页)
第680章 争权逼皇上赏赐(第2页)
但她没有崩溃。她只是缓缓起身,取来朱砂笔,在《补遗录》首页空白处郑重写下:
>**秦婉贞,浙东人,原为宫中女史,因私录先皇后遗诏被定为逆党,于天启七年七月十三日当众焚名于市曹。其女遗落民间,今归宗,名苏清越。**
写罢,她将笔掷于地,仰天长啸:“娘!我找到你了!你的名字回来了!”
那一夜,京城上空雷鸣滚滚,一道紫电劈开云层,直击太庙前的初名碑。守吏惊见碑面浮现无数细小裂痕,每一道都透出微光,拼成一行行陌生名字。经查验,竟是百年前被销毁的《宫婢名录》残迹重现!
与此同时,远在西南的吴县旧衙地下暗室,那三百余页“断嗣者”名单突然自燃。火焰呈青白色,不伤纸页,唯独将“林晚照”三字烧成金痕,随即蔓延至整面墙壁,所有被抹去的女子之名逐一浮现,如星辰点亮长夜。
消息传到昆仑墟,那片手掌形花海一夜盛开,花朵掌心的文字不再是方言故事,而是齐声低语:“秦婉贞……谢昭华……林晚照……我们听见了。”
苏清越知道,这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始。
两年后,她主持编纂完成《全唐女诗辑注》,收录历代佚名女子诗作三千余首。其中一首残篇引得举国泪下:
>“儿啼彻夜寒,吾名谁人唤?
>血书衣襟破,梦中母影残。
>不求身后祭,但愿生时安。
>若得重来日,光照万户门。”
经查,此诗出自前朝一位被赐死的才人,死前用指甲在墙上刻下,后遭泥封。直到今年春雨侵蚀,墙体剥落,才重见天日。
苏清越将其刻于唤名塔第二层,并立碑题曰:“诗存则人存,名立则魂归。”
又三年,北方边境传来喜讯:曾被掳走改称“无名侍”的三百余名女童全部获救。她们被囚于一座隐秘山谷,每日被迫背诵“我不需要名字”“我是主人的影子”。救援队抵达时,多数孩子已失语,只会机械重复那两句话。
但当士兵拿出《补遗录》,逐个念出她们原本的名字时,奇迹发生了??有个小女孩突然抱住书哭喊:“我记得!我叫李招娣!我爹说,我是他最宝贝的闺女!”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孩子们陆续找回自己的声音。有人记起了母亲哼的摇篮曲,有人想起了家门口那棵枣树,还有个盲童摸着书页说:“这个名字……暖的。”
全国为此举行庆典,皇帝亲书“归名日”三字悬于城楼。苏清越受邀致辞,她只说了一句:“请让每个孩子都知道,她们不是‘招娣’‘盼弟’‘来凤’,不是任何人的附属与期盼,而是??她自己。”
台下万人静默,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风波再起。
某日清晨,太庙突发异象:初名碑上的新生儿名字竟开始褪色,无论怎样重刻,皆在一夜间消失。监察司彻查数月,毫无头绪。直至一名老工匠在清理碑底时,发现缝隙中嵌着一片极薄的金属箔,上面蚀刻着复杂符文。
经学者破译,竟是失传已久的“逆愿核咒”片段,作用正是切断新生婴儿与愿核的连接??**让下一代从出生起就成为“无名之人”**。
幕后黑手终于浮出水面:原礼部尚书之子周景和。此人表面支持铭名新政,实则暗中联络二十多个世家,组建“守旧盟”,主张恢复“妇德为本,无名为净”。他认为女性留名导致礼崩乐坏,甚至将近年来干旱归咎于“阴气过盛”。此次行动,便是要从根本上断绝记忆传承。
苏清越亲自带队围捕。当官兵破门而入时,周景和正坐在书房中央,面前摆着一面青铜盘,盘中盛满鲜血,漂浮着上百个纸剪的小人,每个背后都写着一个新生儿的名字。
“你们不懂!”他狂笑,“忘掉才是福!多少女人因记得而痛苦?我母亲记得她被休的羞辱,我妹妹记得她未婚夫悔婚的冷眼!若从一开始就没有名字,她们就不会期待,不会受伤,不会反抗!这才是真正的慈悲!”
苏清越冷冷看着他:“你母亲叫什么?”
“……什么?”
“你母亲的名字。你说她痛苦,那你可曾问过她,是否愿意被忘记?你可曾在她坟前喊过一声‘娘’?还是你也只记得她是‘周门赵氏’?”
周景和怔住,嘴唇颤抖。
苏清越走上前,拿起那面铜盘,将血水泼在墙上。刹那间,血迹扩散,竟自动组成四个大字:
>**赵玉芬,汝子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