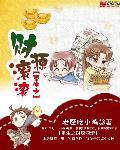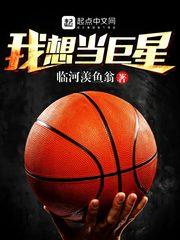笔趣阁>全家夺我军功,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 第683章 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第1页)
第683章 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第1页)
许靖央仿佛能看透他心中所想。
她收回手,负手而立:“乐先生不必惊惶,你弹劾崔尚书,虽与本王立场相左,但亦是出于为国分忧的本意,算不得大奸大恶。”
说罢,许靖央顿了顿,目光扫过乐平川花白的头发。
“况且,先生家中子嗣实在年幼,稚子何辜?眼见你一家老小因此事受累,寒冬流徙,几无生路,本王亦觉不忍。”
山风卷着雪沫,穿过枯枝,透出森寒。
远山笼罩在铅灰色的冷云与弥漫的雪雾中,天地间一片肃杀寒意。
许靖央的话。。。。。。
夜雨初歇,檐角滴水如珠,敲在青石阶上,声声入耳。苏清越独坐书斋,烛火将熄未熄,映得她眉目深沉。林小满离去已三日,可那张清秀面容却如刻入脑海,挥之不去。她翻出《补遗录》中关于林晚照家族的残页,指尖抚过“林氏一脉,断于女嗣”八字,心头骤然发紧。
这不对。
林晚照的女儿确被送往台州乡下,改姓沈氏,婚配农夫,生有一子。此后三代皆为平民,无一人涉足铭名之事。按理说,血脉虽存,记忆早已湮灭。可林小满不仅知晓曾祖母之名,还能平静道出井边紫茉莉的传说??那是连她自己也是重生后才从贝壳密语中得知的秘密。
除非……记忆的传承从未真正中断。
她猛地起身,推开窗扉。春风拂面,带着泥土与花香的气息。远处四明堂灯火通明,几名学子正围坐在碑前诵读《铭心录》,声音随风飘来:“……凡被遗忘者,皆有其名;凡被抹去者,终将归来。”
苏清越闭目聆听,忽觉袖中贝壳微颤。她取出一看,银光竟再度流转,虽不如从前炽烈,却隐隐透出一种新生般的温润光泽。
>“血脉非唯一归途。”
>“记忆自有种子,落地即生根。”
她怔住。
原来如此。她们以为唤醒亡魂、重立碑文便是终结,却忘了最根本的力量??人心中的铭记。当一个人的名字不再只是文字,而成为信念、成为象征、成为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时,它便超越了血缘,挣脱了生死,自行在世间繁衍不息。
林小满不是偶然出现的幸存者,她是记忆复苏的具象化产物,是千万个默默记住“林晚照”这个名字的普通人共同孕育出的新生命。
她当即命人备马,亲赴台州。
一路南行,沿途所见愈发令人心惊。小镇茶肆间,已有妇人教幼女背诵《女史续编》片段;村塾墙上贴着手抄的“四明堂名录”,秦婉贞居首,沈兰音列末;更有老妪在祠堂焚香祷告:“求诸位娘娘护佑我孙女将来能进铭名院读书。”
百姓不再惧怕提及那些曾被禁锢的名字。相反,他们以知晓这些故事为荣,以传颂她们的事迹为责。仿佛一场无声的觉醒正在大地上蔓延,比任何政令都更深远、更彻底。
抵达台州那日,正值清明前夕。苏清越未惊动官府,只带两名随从悄然入城。她直奔城郊一座荒废多年的林家旧祠。据查,此处正是当年林晚照女儿迁居后所建之家庙,后因无人祭祀而倾颓。
然而此刻,眼前景象让她几乎不敢相信。
原本倒塌的门梁已被修缮,院中杂草清除,石阶扫净。祠堂正殿供桌上,赫然摆放着四盏长明灯,灯油未尽,火焰跳动。中央牌位刻着:
**“显妣林氏讳晚照之灵位”**
左右两侧,则分别是“秦氏婉贞”、“谢氏昭华”、“沈氏兰音”。四人并列,香火缭绕。
一名白发老妇正跪于蒲团之上,低声吟唱一首古老歌谣。曲调哀婉,词句却是前所未闻:
>“井底月,照孤魂,
>一夜霜雪百年春。
>莫道人间无记忆,
>紫茉莉开满故园门。”
苏清越缓步上前,轻声问:“老人家,这祠是谁修的?”
老妇缓缓回头,浑浊双眼中竟泛起一丝清明:“是你该问,还是我该问?”她指了指供桌下一只陶罐,“每月初一,总会有人送来新灯油,还有一束紫茉莉。不知是谁,但从不断绝。三年前开始,我就来了,替她们守香火。”
“您认得林晚照?”
“我不认得。”老妇摇头,“但我娘临终前说过一句话:‘咱们家欠一个女人的命,也欠一个名字。若哪天听见井边开花,就得回来还愿。’去年春天,我家后院那口枯井突然长出紫茉莉,我就知道,时候到了。”
苏清越眼眶发热。
她终于明白,这场救赎从来不是她一个人的战斗。无数平凡人,在黑暗年代里悄悄记住了不该记得的事,在沉默中守护了不该存在的记忆。他们或许说不出道理,但他们知道??有些人不该被忘记。
当晚,她在祠中留宿。夜半时分,忽闻庭院有响动。推门而出,只见林小满独自立于月下,手中捧着一束新鲜紫茉莉,轻轻放在供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