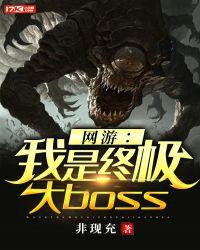笔趣阁>全家夺我军功,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 第693章 被质问拿什么喜欢宁王(第1页)
第693章 被质问拿什么喜欢宁王(第1页)
白鹤回到王府,径直去了书房。
他叩门:“王爷。”
里面传来冷淡的回应??
“进。”
推门而入时,只见萧贺夜端坐于紫檀木书案之后,玄色亲王常服衬得他肩背挺拔如松。
案头堆积的公文在烛光下映出深浅不一的影子。
他执笔的大掌骨节分明,腕势沉稳,眉宇间凝着冷冽。
听闻脚步声,他淡然问道:“将那臭小子揪回来了?”
一看时辰已过傍晚,萧安棠还没有回来的趋势,萧贺夜就猜到,这孩子定是想磨磨蹭蹭在郡主府过夜。
太不像话。
“。。。。。。
暴雨过后,天光微明,紫茉莉堂的残瓦上还滴着水珠。清瞳跪在苏清越灵前,手中捧着那支未写完的笔,指尖微微发颤。她没有哭,只是将笔轻轻放进棺木之中,与那本《静音录》并列安放。
“姑奶奶,”她低声说,“我记住了。”
风穿堂而过,七盏莲灯忽明忽暗,仿佛回应她的誓言。
葬礼之后,三十七位“清”字辈弟子齐聚堂中,一如当年听讲之夜。只是这一次,中央空座无人,唯有那幅《铭心镜》残片静静悬于墙上,蓝光流转,似有低语回荡。
清慧从西域归来,肩披风沙,眼中却燃着不灭之火。“王氏渠”已更名为“兰心渠”,朝廷正式立碑追功,百姓自发建庙供奉。她在西北各地设立女子水利学堂,教少女测算地形、设计沟渠。她说:“母亲们曾用脚丈量山河,如今我们要用智慧改写江河走向。”
清敏在岭南重建“程娘子药井”,广收贫家女为徒,编撰《百草新注》,将民间验方与古医理结合。她不再称自己为“医者”,而自称“传声人”??替那些被毒杀、被流放、被遗忘的女子,把药香重新洒向人间。
清勇卸下铠甲,却未归隐。她主持编修《战史正误》,逐条勘对百年军报,凡有女将功绩被篡者,皆以铁证补录。她更推动朝廷设立“巾帼武科”,允许女子应试授官。第一批女将军已在边关执印,她们出征前必来紫茉莉堂祭拜,口中念的不是兵法,而是沈兰心临终遗言:“他们不怕女人聪明,怕的是女人知道自己聪明。”
清瞳则踏上最艰难之路??她走遍十三道州郡,访查每一首污名化女子的童谣、戏曲、话本。她发现,几乎每一则“红颜祸水”的传说背后,都藏着一个真实的名字:或因才高遭妒,或因志异被囚,或因不肯顺从而被抹黑千年。
她在江南找到一块破碑,刻着“乔静漪之墓”,碑文已被凿毁大半,但底座尚存一行小字:“著《女学启蒙》三十卷,倡女子习六艺,振族兴乡。”当地老人说,这坟原是衣冠冢,真身投井后,家族烧书焚稿,连名字都不许提。清瞳蹲在井边,取出母亲遗留的墨锭,在纸上一笔一画抄下残篇,泪水落在“女子可为相”五字之上,晕开如血。
她开始编写《正谣录》,每一条谣言之下,附上考据、证据、亲历者口述。她写道:“语言是最锋利的刀,也能成为最坚固的盾。我们不说谎,但我们必须说出真相。”
然而,黑暗并未退去。
某夜,京城突降血雨。街头巷尾流传谶语:“妖女摄魂,逆天改命,天地共怒!”紧接着,数座新建女子书院接连遭袭,门窗被泼黑漆,墙壁涂满诅咒。一名年轻女教师在归家途中被人割喉,尸身旁留有一张纸条:“还我祖制清净。”
朝中保守派再度抬头,御史联名上奏:“女学乱纲常,宜速止之!”更有宗室老臣当庭痛哭:“三代以来,妇人不出内庭,今竟令其执兵、掌政、著史!此非盛世之象,实乃亡国之兆!”
少年皇帝震怒,亲自带剑上朝,斩断奏折案几:“朕不信天降血雨,只信人心染毒!谁再诬陷女学者,便是与朕为敌!”
他下令彻查幕后主使,结果令人震惊??竟是几位致仕老臣暗中结社,名为“复礼会”,密谋恢复“妇德律”,废除新政。他们在地下藏书阁中搜出大量手稿,其中一本《女诫新解》竟主张:“女子识字即为淫,读书便是叛。”
皇帝冷笑道:“这些人嘴上说着礼义廉耻,心里装的全是恐惧??怕女人不再跪着,怕历史不再由他们书写。”
他下旨严办,抄没家产,永不录用子孙入仕。同时颁布《女子参政法》,明定女子可任九品以上官职,参与科举殿试,并设“铭功监察司”,专查历代冤案、错案、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