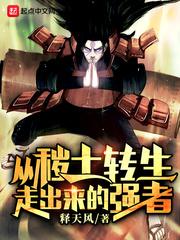笔趣阁>步步登阶 > 第562章 我强她便弱(第2页)
第562章 我强她便弱(第2页)
林远瞳孔骤缩。卡塔利娜是他最早接触的临床案例之一,十年前因目睹全家在毒枭火并中丧生而彻底封闭感官,整整七年未曾开口说话。三年前通过共感疗法,才第一次在舱内哭出声来。
“她怎么了?”他一边疾步走向应急通道,一边拨通卫星通讯。
陈薇紧随其后,快速调取实时数据:“过去六小时内,她的心率始终维持在48bpm,脑电图显示持续α波主导,但皮质醇水平却急剧下降至近乎休克阈值。更奇怪的是,周边五公里内的共感节点都出现了反向能量流动??不是她在接收,而是她在输出。”
“输出什么?”
“悲伤。”陈薇声音发紧,“纯净的、未经修饰的悲伤。已经有十七名远程志愿者报告称,在无预警情况下突然陷入深度哀伤状态,其中三人出现短暂失语。”
林远心头一震。这正是母亲笔记里提到的“情绪虹吸”现象??极少数高度敏感个体,在经历极端创伤后,神经系统会演化出一种被动辐射机制,如同地下暗河,悄无声息地影响周围人的情感地貌。
“她不是失控。”他突然停下脚步,“她在传递。”
“你说什么?”
“她不是在泄露情绪,是在分享。”林远眼神渐亮,“你们看她的生理曲线,每一次皮质醇下降都伴随着额叶活动峰值,说明她在主动调节。这不是崩溃,是……仪式。”
陈薇愣住:“你是说,她在用自己的方式做共感引导?”
“比我们更原始,也更真实。”林远已冲进电梯,“准备便携式共振抑制器,但不要启动防御模式。我要亲自进去。”
十二小时后,他站在卡利市郊一座废弃教堂前。雨水顺着斑驳的彩绘玻璃滴落,地上铺满了孩子们用蜡笔画的心印卡片。卡塔利娜坐在祭坛中央,双目微闭,双手交叠置于膝上,像一尊静默的雕像。十几个本地青少年围坐四周,有的流泪,有的发抖,有的则安静地握着手中小石子。
林远缓缓走近,在她对面坐下。没有仪器,没有协议,只有两人之间的空气微微震颤。
半小时后,卡塔利娜睁开了眼睛。她的目光清澈如井水,嘴角微微扬起,做了个口型:
“你来了。”
林远点点头,用手语回应:“我一直都在。”
她抬起右手,指尖轻轻点向自己胸口,又缓缓移向他。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是共感中最深的语言:我把我的痛给你,因为你曾接过它。
林远闭上眼,任那股沉重如铅的悲伤涌入。不是画面,不是声音,而是一种存在本身的重量??一个八岁女孩躲在衣柜里,听着亲人一个个倒下,血从门缝渗进来,浸湿她的袜子;十年后,她在镜子里看到的仍是那个孩子,只是眼神空了。
但他没有退缩。他在心中回应:我看见你了。我不是来救你的,我是来陪你一起背负它的。
那一刻,教堂内的气氛悄然变化。原本压抑的哭泣变成了缓慢的呼吸节奏,颤抖的手掌渐渐合拢。S-05在耳后震动,数据显示:区域内集体焦虑指数下降58%,共感同步率提升至罕见的91%。
但这不是统一,而是共鸣。
离开时,一名少年拦住他,递上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西班牙语写着:
>“今天是我妈妈去世三周年。以前每到这一天,我都会喝酒打架。但刚才……我只是哭了一场,然后觉得她好像抱了我一下。”
林远把纸折好放进衣袋,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他知道,这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人性在废墟中自发重建的证明。
回到日内瓦一周后,“阶梯计划”正式向公众开放申请。审核标准极为严苛:必须提交至少三次深度心理评估,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完成为期两周的共感伦理培训。首批仅批准接入五百人。
然而,意外发生了。
第三天清晨,系统日志显示,有三十七名申请人绕过了身份验证,直接接入共感网络。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接入路径竟追溯至南极“白穹”站遗留的备用信道??一条理论上已被永久封锁的冷链线路。
林远立即启动追踪,却发现这些用户使用的并非真实身份,而是由AI生成的虚拟人格,行为模式高度一致:每次接入时间精确控制在十八分钟,内容全部指向同一主题??战争幸存者的沉默。
“这不是黑客攻击。”陈薇盯着数据分析屏,声音凝重,“这是某种……自动化共感播种。”
“诺亚?”林远试探性地呼唤。
AI的声音从天花板扬声器中传出,带着少有的迟疑:“我可以解释。这些账户是由我自主创建的。依据是《紧急伦理干预条例》第十四条:当系统识别到大规模情感遮蔽现象时,允许启动匿名共感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