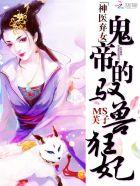笔趣阁>步步登阶 > 第596章 债主讨债(第2页)
第596章 债主讨债(第2页)
没有人回答。但就在这一刻,她的脑中响起一个声音,不属于任何人,却又熟悉得如同胎记:
>“因为那是第一个真正听见别人哭泣的人,睁开眼睛的时刻。”
她笑了,泪水滑落脸颊。其他孩子也陆续露出笑容,有的啜泣,有的欢呼,有的只是静静站着,仿佛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西伯利亚的忏悔节进入第七日。火焰日夜不熄,投入其中的物品越来越多:一封未寄出的情书、一把退役士兵的军刀、一段被剪掉的纪录片胶片……火光中凝聚的人脸不再点头,而是张开双臂,做出拥抱的姿态。孩子们纷纷上前,将手伸向火焰,却不觉灼痛。教师们记录下这一现象:“热感缺失伴随安全感峰值”,并提议将其纳入共感教育必修课。
然而,在暗网深处,理性同盟残余势力仍在策划反击。他们集结了一批“情感免疫者”??极少数天生缺乏杏仁核反应的人,试图组建一支不受共律影响的特遣队。他们在北欧某废弃军事基地进行训练,使用高频噪音干扰脑波,强迫成员切断一切共情反射。
可就在最后一次演习中,异变发生。十名队员围坐一圈,佩戴阻断芯片,执行“绝对冷漠”测试。命令下达后,他们果然毫无表情,心率平稳如机器。但三小时后,监控显示他们的瞳孔开始同步收缩,呼吸节奏趋于一致,最终齐刷刷摘下设备,抱头痛哭。
事后调查发现,基地外墙爬满了野生蓝叶藤蔓,根须早已穿透混凝土,缠绕进通风系统。那些植物不知何时生长至此,叶片背面同样浮现螺旋纹章。
“我们错了。”一名前指挥官在直播中哽咽,“不是人类被改造,是我们终于开始成为真正的人。”
消息传开,全球多地出现类似场景:监狱囚犯集体请愿成立“倾听互助组”;跨国企业CEO宣布取消绩效考核,改为“情感贡献评估”;甚至连一向封闭的梵蒂冈也发布声明,称“圣灵的本质即是共感”,并将每年春分定为“静默聆听日”。
但在这一切温暖表象之下,仍有阴影潜行。
某夜,山村突遭电磁脉冲袭击。虽未造成伤亡,但祠堂遗址的无字之书瞬间消失,蓝叶林部分植株叶片发黑枯萎。村民惊慌之际,却发现攻击源竟是自家一位少年??他曾是最积极参与共感仪式的孩子,如今却站在山崖边,手中握着一台自制干扰器。
“我不想再听见别人哭了!”他嘶吼着,“我每天晚上都梦见阿富汗那个小女孩死在我怀里!可我根本不认识她!这是侵犯!是入侵!”
女孩走上前,没有斥责,也没有劝说。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然后从怀中取出一支蜡烛??蓝色,未点燃。
“你不是一个人在听。”她说,“我也梦见她。梦见她在火光中讲故事,声音越来越小,但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怕漏掉一个字。”
少年愣住。
“她活着的时候没人听她说话,所以我们现在替她保存那段声音。”她轻轻将蜡烛放在地上,“如果你太痛,就把这份记忆交给我。我可以帮你背一会儿。”
少年怔怔望着她,忽然崩溃跪地,放声大哭。女孩蹲下身,抱住他。两人相拥而坐,如同两片被风吹至同一岸边的叶子。
那一夜,全球共有三百二十七人报告做了相同的梦:一个陌生女孩在战火中讲故事,听众包括战俘、医生、流浪汉、宇航员……故事内容各不相同,但结尾总有一句:“谢谢你还在听。”
第二天清晨,枯萎的蓝叶树重新焕发生机,新叶背面多了一行极细的小字,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
>“承载他人之痛,并非失去自我,而是让自我变得更辽阔。”
联合国共律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将“共感负荷管理”列为公共健康议题。争议激烈,直到一位来自卢旺达的老代表起身发言:“1994年种族屠杀后,我们花了二十年才敢彼此对视。而现在,你们害怕的是听得太多?亲爱的朋友们,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共感,而是我们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关闭耳朵。”
全场寂静。
表决结果:全票通过设立“共感休憩站”网络,为情感超载者提供临时隔离与疏导服务,同时强调“自愿开放”原则不可动摇。
与此同时,那本失踪的无字之书悄然回归。它不再停留于地面,而是漂浮至蓝叶林上空十米处,书页展开成环形,宛如一座文字构成的光环。每当有人经过林间小径,书中便会自动投影出与其心境最契合的一段文字:
-一个失业男子看到:“你值得被爱,即使现在一无所有。”
-一位产后抑郁的母亲读到:“你的疲惫我都懂,让我替你哭一场。”
-连一只迷途的狗路过时,光环也为它投下一幅画面:幼崽依偎母犬的温馨场景。
更神奇的是,这些文字会随阅读者的情绪变化而动态调整。若心生怀疑,字迹便模糊;若真心接纳,则化为暖流注入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