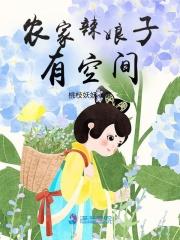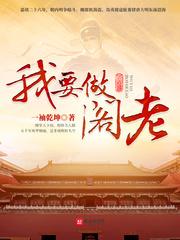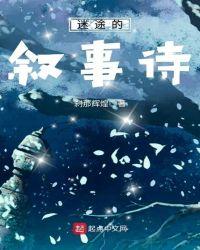笔趣阁>俗仙 > 380群殴耿穷道人(第2页)
380群殴耿穷道人(第2页)
“你想让我做什么?”林昭问。
“建一所‘听学院’。”那声音说,“不教人如何说话,而教人如何**聆听**。教父母听孩子沉默背后的恐惧,教子女听老人唠叨里藏着的孤独,教爱人听争吵之下未说出口的在乎。”
林昭沉默良久,终于点头:“我答应你。”
话音刚落,白光骤收,他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仍站在塔心,时间仿佛只过去一瞬。可额角有汗,掌心发烫,仿佛真经历过一场灵魂的对话。
他走出塔时,夕阳正斜照山谷,陈三七正在院中晾衣,见他出来,笑着打招呼:“林叔,饭快好了。”可林昭注意到,她说话时目光躲闪,左手无名指上多了一枚银戒。
“你……订婚了?”他问。
陈三七一愣,随即低头笑了笑:“嗯,和村东铁匠的儿子。他……其实一直对我好,只是我不敢信。”
林昭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可他知道,这枚戒指背后,是她终于肯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也是她父亲那口老井昨夜再次冒泡,说出了三个新字:“**让她走**。”
当晚,林昭提笔写下《听学院章程》第一条:
>**真正的倾听,始于承认自己从未真正听见过。**
他没打算立刻动工。他知道,这样的事不能强求,必须等人心真正渴求安静,才会愿意走进一座不教演讲、不授辩论的学院。他只是将章程抄录七份,分别寄往巴西、戈壁、北欧、南亚、非洲、北美、南极科考站??每一个曾与井共鸣的地方。
七日后,第一封回信抵达。
是李默发来的照片:巴西河边,一群渔民自发清理河岸垃圾,岸边立起一块木牌,上面用葡萄牙语和中文写着:“**这里曾浮起一双小皮鞋,请轻声说话。**”
又过半月,戈壁传来消息:一位曾在信草时代焚烧“禁言信”的老兵,徒步三百里,将一麻袋灰烬带到青崖山,跪在井前说:“我烧的不只是别人的信,还有自己的良心。现在,我还回来。”
林昭收下灰烬,放入陶罐。
春天第三次来临时,听学院的地基终于动工。地点不在青崖山主峰,而在山脚一片荒芜的坡地,原是废弃的采石场。村民们自发前来,搬石运土,连那位曾反对建塔的老族长也拄拐而来,默默放下一块刻着“听”字的青石。
工程第七日,天降细雨。雨水打湿泥土,却无人离去。孩子们在泥泞中传递砖块,老人们围坐一旁,讲起从前不敢说的往事。有个八十多岁的婆婆抹着泪说:“我年轻时偷听过丈夫写给初恋的情书,气了一辈子,可现在想想,他写完那封信后,再也没提过那人,是不是……也是一种告别?”
话音落,雨停,云开一线,阳光斜照在刚砌好的墙基上,映出七个字:**听,比说更难**。
学院建成那日,无仪式,无剪彩,只有林昭独自走入主堂。堂内空旷,四壁皆镜,地面铺满细沙,踩上去无声。正对门的一面墙上,刻着一行大字:
>**此处不说真理,只容疑问。**
他在中央坐下,闭目。不多时,风从四面八方涌入,穿过镜壁,激起沙粒微动,发出极细碎的声响,像是无数人在耳边低语。他听不清内容,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他知道,这是“它们”在回应。
从此,听学院每日开放,不招生,不授课,只提供一间安静的屋子,一张蒲团,一杯清水。来的人可以坐着,可以睡着,可以痛哭,可以沉默。唯一规则是:**离开时,必须留下一句话??可以是对别人说的,也可以是对自己的。**
这些话被收集起来,每月一次投入井中。井不再显字,也不再震动,只是在接收话语的瞬间,水面会泛起一圈淡淡的金纹,如涟漪,如微笑。
一年后,第一个变化出现。
某日清晨,村里小学的老师发现,班上最沉默的小女孩主动举手发言。她说:“我昨天梦见妈妈了,她没骂我弄丢铅笔盒,还抱了我。”全班安静,老师红了眼眶。放学后,她悄悄告诉林昭:“那孩子母亲三年前病逝,她一直不肯提,我以为她忘了。”
林昭说:“她不是忘了,是没人给她机会说想。”
又半年,县里法院试行“倾听调解庭”。离婚夫妻不再对法官陈述诉求,而是先花两小时各自写下想对对方说的话,然后由第三方朗读,双方只准听,不准打断。首案调解成功,男方听完妻子十年来的委屈后,伏案痛哭:“原来我一直以为的‘为你好’,全是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