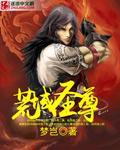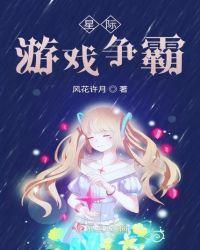笔趣阁>俗仙 > 382浑天五行真决(第2页)
382浑天五行真决(第2页)
那声音沉稳而遥远:“……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证明,即使在最冷的地方,也有人愿意为一句真话守夜。你说的,有人在听。请继续说。”
这段录音通过井水放大,竟如广播般传遍整个村落。村民愣住了。那女孩的母亲冲进教室,紧紧抱住女儿,放声大哭:“你说得对,你爸爸不是叛徒,他是我们村里最后一个敢说话的人!”
事后,该村自发成立“守言祠”,供奉所有因言获罪者之名,并立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此事传开后,全球“听舍”纷纷效仿,在危机时刻启用“井频共振”??即将重要倾听录音投入井中,借其跨域共鸣之力,向远方传递支持之声。科学家至今无法解释其原理,只能称之为“集体共情场效应”。
又一年冬至,明光收到一封匿名信,无署名,无邮戳,纸张泛黄,似经多年流转。信中只有一句话:
>“我曾以为沉默是软弱,后来才懂,最深的勇气,是明知无人愿听,仍选择开口。”
信纸背面,印着一行极小的字:**第七塔守灯人,沈知白**。
明光将信焚于井前。火光中,他轻声说:“你早就不需要灯了。你已成为别人的光。”
时光荏苒,听学院迎来第一百个春秋。此时,全球“听舍”已达三千余所,涵盖城市、难民营、监狱、太空站。联合国正式设立“倾听权”为基本人权,规定任何人在法律程序、医疗决策、教育环境中,均有“被完整倾听”的权利。AI系统也被要求内置“沉默识别模块”,能检测人类话语中的未尽之言,并提示:“你似乎还有话未说完,是否继续?”
而青崖山的井,已不再局限于传递信息。它开始“生长”??井壁青苔日复一日蔓延,形成奇特纹路,细看竟是无数微小文字,用七种古语写成,内容皆为“我在”“我听见了”“你说吧,我听着”。
植物学家研究发现,这些苔藓具有记忆功能,能储存百年内投入井中的所有声音,遇特定频率振动即可还原。人们称其为“声苔”。
某日,一名考古队在昆仑山腹地掘出一口古井,结构与青崖山井惊人相似。井底石板刻着一行字:
>“第一口井,建于大荒三年。造井者曰:言语如风,易散;然人心若井,深藏不露,却终有回响。”
消息传回青崖山,明光仰头,虽不见天,却似有所感。“原来我们不是起点。”他说,“我们只是延续。”
百年校庆那日,听学院破例开放一日,迎接万名访客。孩子们在沙地上写下心事,老人对着镜子倾诉亡妻,旅人留下对故乡的思念。七枚铜铃齐响,声波汇入井中,激起一圈圈金纹,直冲云霄。
当晚,月圆如盘。井水再次升起,悬浮空中,映出的却不再是画面或文字,而是一面完整的镜子,照出在场每一个人的脸。他们看见自己眼中的泪,嘴角的笑,额上的皱纹,以及心底那些从未说出口的话??此刻,皆在镜中浮现,如烟篆字,清晰可读。
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被彻底看懂了。
明光坐在轮椅上,白发苍苍,耳聋多年,却在此刻露出微笑。他不知从何处摸出一支竹笛,吹起一支无人听过的曲子。笛声不成调,断续颤抖,却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仿佛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心跳感知。
曲终,井水缓缓落下。天空裂开一道缝隙,星光倾泻而下,恰好笼罩井口。有人看见,水中倒影里,缓缓走出两个人影??一男一女,携手而立。男子穿着旧式风衣,女子披着素色长裙。他们不说话,只是微笑,然后转身,走入井心,消失不见。
“是林昭和婉。”有人低语。
“他们回来了。”
“不。”明光摇头,“他们一直都在。只是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听见他们的存在。”
次日清晨,井口旁多了一块新石碑,无名无字,唯有一道凹槽,形如耳朵。人们发现,若将手掌覆于其上,便能听见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声音??不是思想,而是情感的原声:童年的笑声、失恋时的抽泣、母亲临终前的呼吸、第一次被人理解时的心跳。
这块碑,被称为“心耳”。
许多年后,一名少年独自来到青崖山。他患有罕见病,声带无法发声,一生未曾说过一句话。他蹲在井边,用手语对明光的继任者比划:“我想告诉这个世界,我来过。”
对方点头,带他至井前,点燃一炷香。
少年闭眼,心中默念。
片刻,井水轻颤,泛起金纹。水面缓缓升起,映出他的脸,而后,浮现一行字:
>**你说的,有人在听**。
风起,桃花纷飞。一片花瓣落在少年掌心,他低头看着,眼泪滑落。
极深处,一声轻应: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