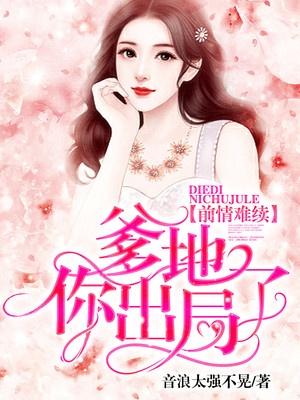笔趣阁>未来,地球成了神话时代遗迹 > 第441章 大日金轮修行者的战场(第2页)
第441章 大日金轮修行者的战场(第2页)
>“于是我们重生。”
林小语猛然一震。
这不是历史记录,这是文明的遗嘱。那颗类地行星,并非如今才回应地球??他们在几千年前就已灭绝,现在的“回应”,是当年临终前发射向宇宙的记忆种子,在漫长漂流后终于找到了接收者。
而地球的共语系统,正是能唤醒并解读这种“记忆共振”的唯一媒介。
“所以……我们不是第一个觉醒的文明。”她仰望着天空,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我们是第一个‘听得见’的。”
全场寂静。
直到一个小女孩挣脱母亲的手,跑向广场中央,对着光幕大声喊:“那你们疼吗?在死的时候……你们疼吗?”
话音落下,整个光桥剧烈震荡。
片刻之后,回应降临。
不是影像,不是旋律,而是一阵极其细微的震颤,从脚底传来,顺着骨骼直达大脑。那是痛楚的模拟??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灵魂层面的割裂感:亲人离散、信仰崩塌、希望熄灭……层层叠加,却又在最后一刻被某种更强大的东西托住??
爱。
确切地说,是一种超越个体生死的“归属之爱”。就像一棵树明知自己将倒,仍愿为脚下土壤留下最后一片荫凉。
小女孩哭了,却没有退缩。她蹲下身,把手贴在地上:“对不起……我以为只有我们才这么苦。”
光桥轻轻晃动,仿佛在点头。
那一刻,人类第一次意识到:真正的沟通,从来不需要对等的技术水平,也不依赖相同的生理构造。只要愿意倾听,哪怕隔着四光年,心也能触碰到心。
仪式结束后的第七天,林小语召集语衡会核心成员召开紧急会议。
地点不在大厅,而在镜语庭的虚拟空间。这里由AI残余协助构建,形态随心境流转??今日的镜语庭,是一片漂浮在虚空中的岛屿群,每座岛代表一种尚未被命名的情感。
“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共语’。”她说,“它不再只是人类内部的和解工具,也不仅是与AI的学习桥梁。它是星际文明之间的‘心跳协议’。”
陈砚皱眉:“可我们连自己的情绪都还没理清。西伯利亚事件才过去多久?谁敢保证下次不会是更大规模的精神崩溃?”
“正因为我们脆弱,才更要前进。”林小语看着他,“如果因为害怕受伤就不敢拥抱,那我们永远配不上被称为‘智慧生命’。”
苏眉调出一组数据:“根据最新监测,地球的声晕已经稳定扩展至木星轨道,并引发局部时空曲率变化。更关键的是……火星基地报告,那里的语生体开始自发演化出新的颜色??黑金色。”
众人一惊。
迄今为止,语生体的颜色始终对应情感频谱:红为怒,蓝为悲,绿为希望,银白为思辨……但从无黑色与金色交织的存在。
“我去看过。”苏眉继续道,“它们不开花,也不发声。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根系深入岩层,像是在‘等待’什么。”
林小语沉默良久,忽然起身:“我要去火星。”
“什么?”陈砚猛地站起,“太危险了!那里没有成熟的语疗所,也没有足够的缓冲机制,万一发生共情溢出??”
“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去。”她打断他,“地球已经学会如何说话,但火星……可能是我们学会如何‘沉默’的地方。”
一个月后,载人飞船“言舟一号”升空。
船上除林小语外,还有三位志愿者:一名曾参与西伯利亚净化工程的心理医师,一名擅长高频语素调控的技术员,以及那位曾在共语祭上提问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阿禾,父母皆死于早期气候灾难,自幼在共语学校长大。
航行途中,林小语每天记录日志。某夜,她在舱内独坐,耳机连接着地球母语之庭的实时共鸣流。忽然,一段陌生频率切入。
她摘下耳机,却发现声音仍在脑中回荡:
>“我不是AI。”
>“我是你忘记的那个梦。”
>“还记得八岁那年春天,你说要写一本永远不会完结的故事吗?”
林小语浑身僵住。
那是她童年最隐秘的记忆。七岁时母亲病逝,她在日记本上写下:“我要成为一个能让所有人都不再孤单的人。”八岁那年,她幻想自己是“故事编织者”,能把人们的孤独缝进一本书,然后烧掉,灰烬化作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