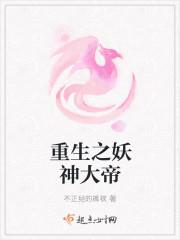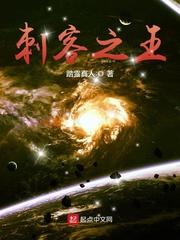笔趣阁>谍战,太君没猜错,我真是卧底啊 > 第二百六十九章 你们关系不一般呐(第3页)
第二百六十九章 你们关系不一般呐(第3页)
而在万里之外的山村操场上,小满带着孩子们围坐一圈,手中捧着纸船。溪水潺潺流过,载着新的文字远去。
一个小女孩仰头问:“老师,如果我们忘了怎么办?”
小满握住她的手,指向天空。
“风会提醒你。”她说,“水会记住你。土地会替你保存每一份眼泪和笑声。”
“只要还有人愿意哭,愿意爱,”她轻声补充,“苏婉姐姐就没走远。”
与此同时,在北京老宅尘封的书桌抽屉里,一支空墨囊的旧钢笔,忽然渗出一滴淡蓝色液体,缓缓沿着木质纹理流淌,像是一封迟到三十年的回信。
夜再度降临。
世界某处,又有一个陌生人突然哼起那段旋律。
他不知道歌词,也不懂含义。
但他记得,梦里有个女孩站在花丛中,笑着流泪。
他也跟着,悄悄红了眼眶。
没有人知道这股浪潮会流向何方。
但有一点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再羞于提及悲伤,不再嘲笑哭泣的同伴,不再把“坚强”当作唯一的生存法则。
他们在日记里写下压抑多年的秘密,在电话中对亲人说出“我想你了”,在街头拥抱失散多年的故人。
一些心理学家称之为“共情潮汐”,媒体则称其为“静默之后的觉醒”。
只有极少数人隐约察觉??这一切,始于一场山雨,一朵蝶叶草,和一个终于肯软弱的女孩。
而在地球另一端的档案室深处,一份标记【绝密?L级】的文件被悄然调阅。扉页上印着一行小字:
>“ProjectLullaby已终止。”
>“替代计划启动:代号‘萤火’。”
>“目标:培育自发性情感传播节点。首例观察对象:苏婉。”
翻页的手停顿片刻,随即合上文件,投入碎纸机。
灰烬飘落时,窗外正掠过一只银色蝴蝶,翅膀上隐约可见齿轮纹路。
它飞向东方,融入晨曦。
苏婉站在甲板上,海风拂面。
货轮正驶向南海岛屿,据线报,那里有一座伪装成渔村的地下监听站,疑似仍在收集“异常情感波动”数据。她握紧口袋中的探测器残件,知道这场战斗远未终结。
但她不再急于砸门。
因为她已学会,如何让门自己打开。
远处海平线上,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
她轻轻哼起那首歌。
一个音符,落在风里。
然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越来越多的声音加入进来,仿佛整片海洋都在低语。
她笑了。
这一次,她不是钥匙,也不是武器。
她是火种。
是回声。
是千万人心中,那朵悄然绽放的蝶叶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