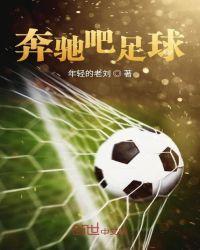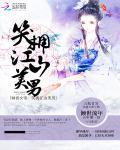笔趣阁>婚后上瘾 > 第398章 陆 魏 茜茜该回家了(第2页)
第398章 陆 魏 茜茜该回家了(第2页)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里,袁晨曦没有讲任何专业术语,也没有急于安慰。她只是陪着,一句句回应,一次次确认她的感受是否被理解。直到女孩断断续续说出这几天的恐惧:父亲扬言要烧掉母亲遗物,她试图阻止却被推倒在地;她不敢报警,怕“家被拆散”,可又害怕自己也会像妈妈一样“消失”。
“你不是累赘,也不是错误。”袁晨曦一字一句地说,“你是这个家里唯一坚持留下来记住她的人。这很勇敢,也很珍贵。”
随后,小岩接入语音,用方言缓缓说道:“小舟,我是小岩哥哥。你还记得我们约定的暗号吗?当你摇铃三下,就代表你需要支援。现在,我告诉你??整个‘回声网络’都在为你摇铃。”
窗外,天边泛起鱼肚白。救援队已抵达小屋外,轻声呼唤。当女孩颤抖着打开门的那一刻,晨光洒在她脸上,照见久违的泪与释然。
袁晨曦靠在椅背上,终于松开一直紧握的拳头。她看了眼时间:清晨五点零九分。这场跨越千里的倾听,持续了近三个小时。
她没有回房休息,而是打开邮箱,将此次事件整理成案例简报,附上处理流程与心理干预记录,标记为【紧急共享】发送至全国三百余名核心成员。
随后,她在日记本上新增一页:
>**5月6日晨**
>今夜,我们救了一个孩子,也再一次被她拯救。
>她让我明白,所谓系统,并非冰冷的技术堆叠,
>而是一个个愿意彻夜守候的灵魂,串联起的光链。
>
>小舟开门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念安问我的问题:
>“妈妈,为什么坏事情总发生?”
>我说:“因为世界不完美。”
>他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努力?”
>我答:“因为我们可以让它少一点不完美。”
>
>今晨的日出格外明亮。
>像是一种承诺:只要还有人在等,我们就不会停止奔赴。
上午九点,袁晨曦出现在“回声谷”多功能厅,主持本周例会。孩子们正在隔壁教室进行艺术疗愈课,笑声隐约传来。她站在投影幕布前,讲述昨夜事件全过程,重点分析基层联动机制的反应效率。
“这次成功的关键,不是我,也不是某个专家,而是‘悄悄话小屋’的存在本身。”她看向在场所有人,“它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即使最封闭的孩子,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信号。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永远保持接收状态。”
会议结束时,朵朵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幅水彩画:“袁妈妈!这是我画的‘回声守护者’!”
画中,一群穿着不同制服的人手拉着手,围成一圈保护着中间的小孩。每个人胸前都挂着铃铛,天空飞着写满话语的纸鸢。最左边的男人轮廓分明,袖口卷起,正蹲下身子倾听??显然是聿战。
袁晨曦笑着抱起她:“真好看。”
“爸爸昨晚都没睡觉!”朵朵嘟嘴,“他说要改应急预案,还打电话给太阳能公司,说要把所有小屋的电池容量翻倍。”
袁晨曦心头一暖。她知道,聿战从不说“我爱你”,但他把爱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比如为千里之外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孩,彻夜修改供电方案。
中午,她刚端起饭盒,手机震动。是一条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消息:日内瓦会议后的提案已被纳入全球心理健康行动试点名录,中国“回声模式”将在东南亚三国开展初期合作。
她还没来得及回复,聿战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保温桶。“陈然说你没吃早餐。”
她无奈一笑:“你怎么总把我当病人照顾?”
“因为你总是忘了自己也需要被照顾。”他打开盖子,是她最爱的南瓜小米粥,温度正好。
两人坐在走廊长椅上吃饭,阳光斜照,铃铛轻响。远处,念安正教几个新来的孩子编守护结,动作认真得像个真正的小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