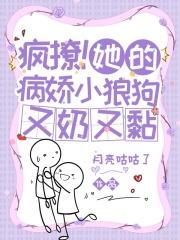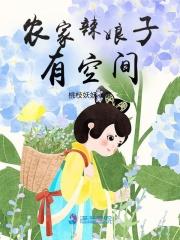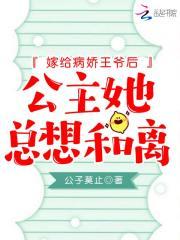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我是县城婆罗门 > 第404章 抬起来点(第1页)
第404章 抬起来点(第1页)
颜理突然收到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
虽然沈安安那一套理论十分荒诞,但确实是沈安安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她不知道要怎么去说。
或许沈安安是好心吧,虽然是那种荒诞的好心。
但无形。。。
夜风穿过松涛阁的檐角,发出低沉呜咽,像是无数未尽之言在山间徘徊。阿诺站在地窖口,手中红木箱的重量仿佛不是来自木材与纸张,而是三十年前那一夜母亲独自扛起的命运。他没有立刻下山,而是将箱子轻轻放在石台上,打开日记本,一页页翻过那些泛黄的字迹。
每一页都像一把钥匙,开启一段被尘封的记忆。杨秀兰写下的不只是个人遭遇,更是一份沉默的控诉??关于圆桌会议如何以“社会稳定”为名,启动“影户行动”;关于她如何在被捕前四十八小时,冒着生命危险将关键数据加密嵌入共感网络底层;关于她在审讯室里一次次重复“我愿意忘记”,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让那段坐标信息能随着她的脑波频率悄然扩散。
>“他们以为我是工具,可我也曾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我不求赦免,只求有人记得。”
最后一句话下面,画着一道歪斜的横线,墨迹已干涸多年,却仍透出执拗的力量。
阿诺合上日记,抬头望向星空。庐山的夜空清澈得近乎透明,银河如练,横贯天际。他知道,此刻全国有八亿人正通过共感终端接收着同步推送的历史档案:1327位受害者生平、影户计划原始文件、谢知远与林素贞早年通信记录……一场前所未有的记忆复苏正在发生。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开始浮现。
第二天清晨,清河县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一位卖豆腐的老伯蹲在摊前摇头:“讲这些旧事做啥?人都死了,揭出来又能怎样?”茶馆里几个退休干部低声交谈:“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提‘清算’,这不是挑动对立吗?”甚至有家长打电话给学校,要求屏蔽纪念馆参观课程,“别让孩子心里种下仇恨”。
这些言论迅速在网络发酵。微博热搜出现新词条:#我们真的需要记住一切吗#。支持者称这是民族觉醒的开端,反对者则警告“过度追责将撕裂社会”。更有境外势力趁机煽风点火,宣称“中国陷入历史复仇狂潮”,呼吁国际干预。
阿诺坐在返程车上,看着手机屏幕不断弹出舆情报告,眉头紧锁。
小禾来电时,他正驶过清河大桥。
“中央成立了‘记忆重建特别工作组’。”她的声音冷静而疲惫,“高层意见分歧很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面公开,另一部分坚持‘适度披露’,防止情绪失控。最后折中决定:建立国家记忆博物馆,但部分内容列为‘延迟解密’,最长可达五十年。”
“五十年?”阿诺冷笑,“等那时,所有亲历者都已不在了。”
“不仅如此。”小禾顿了顿,“国务院办公厅刚刚发布通知,禁止任何个人或组织擅自传播未经核实的‘影户相关材料’。违者将以‘扰乱公共秩序’论处。”
阿诺猛地踩下刹车,车子停在桥中央。
风从河面吹来,带着初春的寒意。
他忽然明白??胜利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场斗争的起点。
真正的敌人从未消失。他们换上了温和的面孔,说着“理性”“克制”“向前看”的话语,却依旧试图掌控谁可以被记住,谁必须被遗忘。
三天后,国家记忆博物馆奠基仪式在原县委大院遗址举行。礼炮鸣响,红旗升起,镜头对准了主席台上的政要们微笑的脸庞。记者们争相拍摄这一“历史性时刻”。唯有阿诺站在角落,目光落在那口废弃水井的位置??那里已被围栏圈起,铭牌上写着:“共感网络起源地”。
仪式结束后,他独自走入工地深处,在井边蹲下身,用手拂去泥土。
突然,指尖触到一块异样的金属片。他小心挖出,竟是一截残破的数据接口,型号古老,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军用级神经链接装置。
“这里曾经连接过什么……”他喃喃道。
当晚,他在临时办公室对接口进行逆向解析。当驱动程序加载完成,一段隐藏日志缓缓浮现:
>【1994。12。2103:15】
>实验体B-07接入“昆仑-7”原型机。
>意识上传进度:3%……12%……48%……
>突发脑电风暴!系统自检失败!
>警告:情感溢出阈值突破!
>强制断开连接。
>实验体B-07宣告临床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