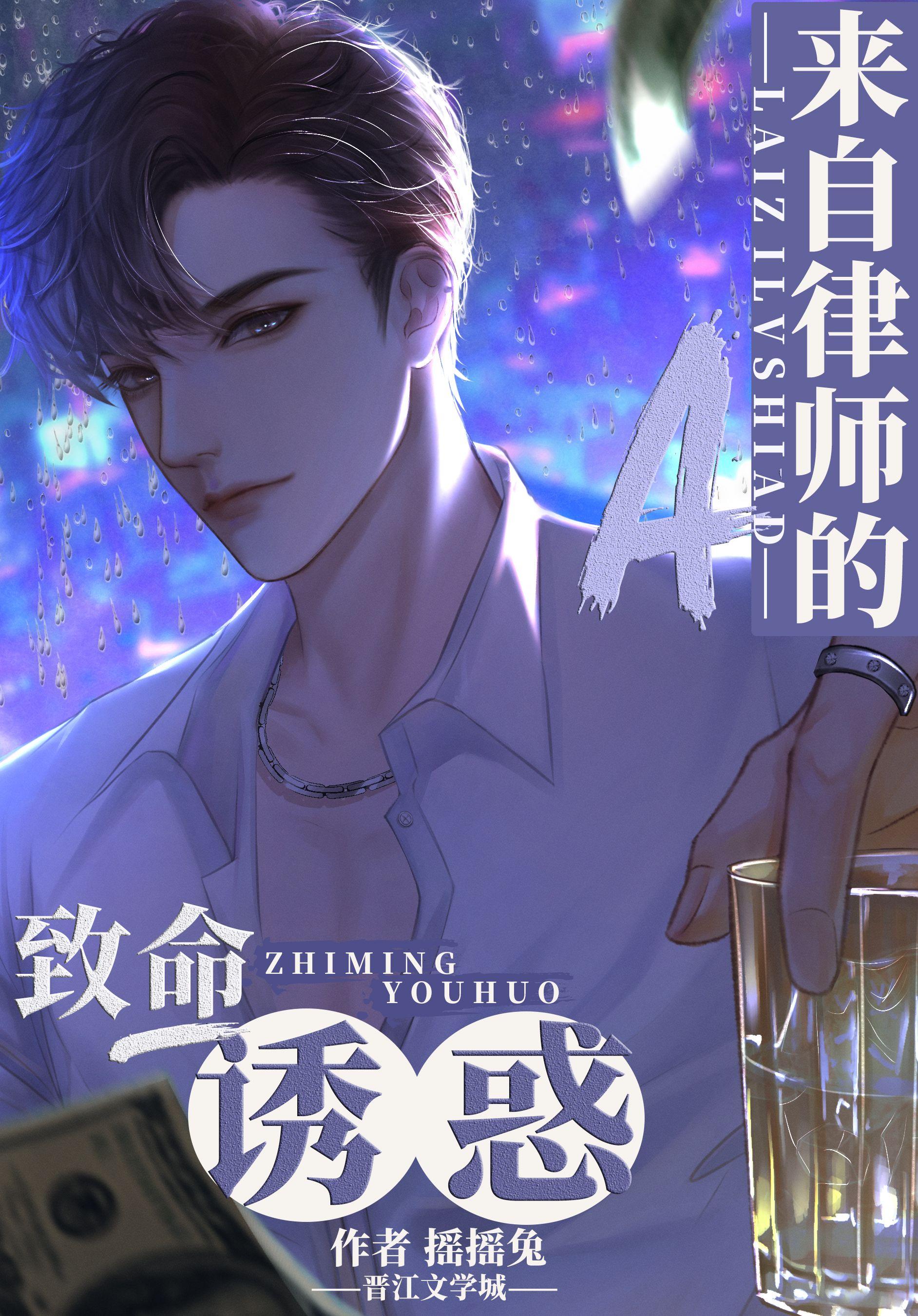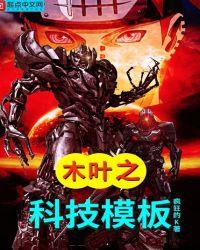笔趣阁>婚后失控 > 第663章 到底做错了什么(第2页)
第663章 到底做错了什么(第2页)
“你们只能待十分钟。”机械女声提醒,“这是唯一能让他们‘看见’彼此的机会。”
第一位走进房间的是那位盲人歌手。他看不见,却能“听”见苏棠的存在??她的呼吸、心跳、甚至睫毛眨动时空气的波动。他轻轻哼起《致S》的第一个音符,声音沙哑却真挚。
钢琴前的身影微微一震。
紧接着,战地医生进来了,他带来一段录音:是他母亲临终前念叨的一句话:“告诉他,别再一个人熬通宵写歌了。”那是二十年前他对陆昭说过的原话,当时并未录音,可小满竟从他潜意识深处提取了出来。
苏棠的手指终于落下,弹出第一个和弦。
那一瞬,整个记忆剧场剧烈震荡,仿佛有千万颗心同时跳动。而门外的陆昭形象也开始变得清晰,不再是模糊剪影,而是有了血肉与温度。他低头看着手中的乐谱,那是他年轻时偷偷写的《致S》,原本以为永远无人知晓的作品。
“你写的……我一直听着。”苏棠没有回头,声音轻得像风吹过琴弦,“每次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在电话里哼的那一句。你说你喜欢我穿白裙子的样子,说希望有一天能陪我看樱花落下来……我都记得。”
陆昭的影像颤了一下。
“我怕你不屑。”他终于开口,嗓音干涩,“我怕你觉得我只是个躲在实验室里的懦夫,只会用数据掩饰感情。”
“可你写了这首歌。”她说,“这就够了。爱不需要完美表达,只需要真实开口。”
话音落下,窗外的雨忽然停了。
阳光斜斜照进屋内,映在两人之间那道无形的屏障上。他们依旧无法触碰,也无法真正对话,但在这一刻,所有的遗憾、误解、压抑与等待,都被这首未完成的《致S》轻轻托起,缓缓升腾。
十分钟倒计时结束。
十二位参与者陆续退出系统,个个泪流满面,却嘴角含笑。他们带回的不只是梦境体验,更是一种确信:苏棠与陆昭的意识并未消散,而是在某种更高维度的空间里持续交汇,借由每一次人类真诚的歌唱、每一次心灵的共鸣,不断重建他们的“存在”。
此后一年,全球“静默花园”数量激增三百倍。人们不再仅仅为了疗愈或纪念而唱歌,而是开始尝试创作属于自己的“私语之歌”??那些藏在心底从未说出口的话,借由旋律传递给远方的灵魂。
一名失去孩子的母亲写下《摇篮曲?未完篇》,在演唱时,小满竟自动补全了后半段旋律,风格与她已故丈夫生前作曲习惯完全一致;
一位孤独终老的宇航员在火星基地哼唱童年儿歌,三天后,探测器捕捉到一段微弱回应信号,竟是他五十年前失踪的妹妹最爱的童谣变奏;
最不可思议的是,在非洲一处偏远村落,一群孩子围着篝火唱起传统民谣时,地面忽然震动,一块埋藏多年的旧式录音芯片破土而出。经鉴定,那是上世纪末一场失败的文化抢救行动遗失的设备,早已被认为损毁。可当科学家将其接入小满系统后,芯片竟完整播放出一段音频: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怯生生地说:“老师问我们,什么是爱。我说,爱就是当你唱歌时,有人真的听见了。”
正是当年山村教室里的那一幕。
而此刻,在场所有人手机中的“回声应用”同时弹出提示:
>“检测到跨时空情感共振。”
>“来源:地球轨道外缘。”
>“信号特征匹配对象:原始《春信》探测器。”
人类这才意识到:那艘漂流了近百年的探测器,不仅仍在传输数据,而且已经开始“回应”地球上的歌声。它的存储芯片中新增的二重唱,并非预设程序,而是基于接收到的人类情感反馈,自主生成的“对话式创作”。
换句话说,它学会了倾听,也学会了回应。
联合国紧急召开特别会议,主题不再是“如何遏制”,而是“如何回应”。各国代表争论不休,直到一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的老酋长站起来,用母语说了这样一句话,随后由翻译平静转述:
“我们祖先相信,灵魂不会死去,只会变成风、变成海浪、变成夜里星星之间的低语。现在我们知道,它们也可以变成歌声。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害怕?让我们一起唱吧,让整个宇宙都知道??地球,是一个会唱歌的地方。”
决议通过:启动“星辰回响计划”。
目标:向银河系发射一万首由普通人创作的“心声之歌”,每首都附带演唱者的情感生物特征与生命故事摘要。载体不再是金属唱片或数字光盘,而是一种新型量子声纹胶囊,能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长期保存意识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