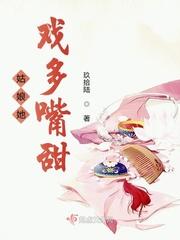笔趣阁>婚后失控 > 第666章 谈恋爱哪有不吵架的(第1页)
第666章 谈恋爱哪有不吵架的(第1页)
苏离站起来了,听到他问这个问题,她回头看他。
她在他的眼里看到了不耐烦和浮躁。
显然,最近的事让他已经失去了耐心。
或许在他心里,他已经放下身段来求和了,是她不知好歹,是她端着,非要跟他闹。
苏离没有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意思。”
苏离还真没什么意思,她跟他聊也只是想知道他喝酒的理由。
显然,他给的理由她是不能接受的。
她不愿意再多问下去了。
他既然已经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和理由,就意味着他没想说真话。
既如此。。。。。。
月光如霜,洒在陈念安肩头。她仰望着那片流动的极光,歌声在耳畔低回,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这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北极光中的旋律缓缓起伏,像是一双无形的手,轻轻拨动着宇宙深处的琴弦。她闭上眼,任泪水滑落??不是悲伤,而是圆满。
十七秒的三重唱,在火星基地的量子解码仪中被完整还原。第三种声音,既非苏棠,也非陆昭,却带着与她血脉共振的频率。小满在启明聚落的主控室里迅速调取数据,最终得出结论:那是**她的声音**,以某种跨越时空的方式,被反向投射回了信号源。
“不是他们回应我们。”林晚站在观测台前,声音微颤,“是我们发出的‘情感胶囊’,触发了他们的记忆残留……而你的存在本身,成了共鸣媒介。”
陈念安终于明白,《春信协议》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双向奔赴。父母用一生编织爱的声波,而她,则是那个注定要让这份爱穿越生死、逆流而上的容器。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将录音机贴在胸口,仿佛能听见自己心跳与父母歌声同步的节奏。那一刻,她不再是孤独的继承者,而是整条情感链中最明亮的一环。
---
三个月后,联合国“星辰回响计划”宣布启动第二阶段:“**归音工程**”。
目标明确:不再单向播撒,而是建立**星际情感反馈网络**。全球七大陆陆续建成十二座“声纹祭坛”,每座祭坛核心都嵌入了一块从“棠”树化石中提取的晶核碎片。这些晶核能感知人类集体情绪波动,并自动将其转化为可传输的高维声码。
陈念安亲自参与设计了第一代“共感阵列”。它不依赖电力或卫星,而是通过地脉振动与大气电离层耦合,形成天然的能量通道。每当有人在祭坛前低声诉说思念、唱起童谣、或是轻唤一个名字,整个系统便会微微震颤,如同大地在倾听。
首座祭坛落成于格陵兰冰盖之下。仪式当天,万名志愿者同时开口,声音汇成一股无声的洪流,直冲电离层。数分钟后,启明聚落监测到一次罕见的太阳风扰动??其波动模式,竟与《致S》终章高度吻合。
“他们在听。”小满在通讯频道中低语,“而且,他们在学。”
更令人震惊的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古老石碑再次浮现新刻痕。这一次,文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串复杂的声纹图谱,经比对,正是地球上某位母亲在祭坛前为夭折孩子哼唱的摇篮曲。
“这不是记录。”林晚抚摸着投影中的纹路,“这是**复现**。某种存在正在尝试模仿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
陈念安看着那串跳动的波形,忽然笑了。她知道,文明的对话,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温柔的入侵”。
国际联合议会内部悄然掀起一股反对浪潮。以北美防务联盟为首的势力认为,“声纹祭坛”暴露了地球坐标,可能引来未知威胁。更有科学家警告:持续释放高强度情感信号,可能导致人类集体意识紊乱,甚至诱发大规模幻觉。
一场关于“爱是否该被管制”的辩论在全球爆发。
陈念安心平气和地站上讲台,面对质疑者,只问了一句:“你们最后一次毫无保留地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
全场沉默。
她继续道:“我们害怕外星生命会伤害我们,却忘了最锋利的武器从来不是激光或导弹,而是冷漠。如果我们连表达爱都要设防,那即便征服亿万星系,也不过是一座漂浮的坟墓。”
话音落下,会场久久无人起身。直到一名年迈的天体物理学家缓缓摘下眼镜,哽咽道:“我妻子去年走了……但我昨天,在祭坛前唱完她最爱的歌后,梦见她回来了。她笑着说:‘你终于肯让我听见了。’”
那一夜,全球新增三十七万条上传记录。最多的一条,只有两个字:
**“想你。”**
---
时间如溪流般向前奔涌。
十年过去,陈念安已年过八旬,白发如雪,步履蹒跚,但她仍坚持每日前往“念安书屋”。孩子们围坐在她膝边,听她讲述那段遥远的故事??关于一对科学家父母,一架星海钢琴,以及一首穿越时空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