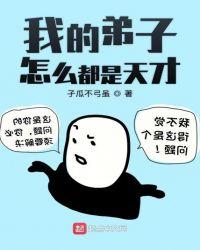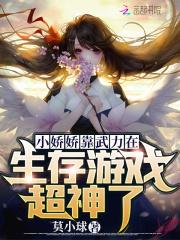笔趣阁>婚后失控 > 第701章 莫行远躲着苏离(第3页)
第701章 莫行远躲着苏离(第3页)
苏离摸着她的头发,轻声道:“不是赢,是终于可以说真话了。”
当晚,“母亲之桥”举办庆祝活动。五十多位受益母亲齐聚一堂,每人点亮一支蜡烛,围成心形。她们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有的哽咽难言,有的泪中带笑。
轮到苏离发言时,她举起手机,打开那张雪地里的全家画??树根深扎冻土,枝头盛开铃兰。
“我们常说要忘记伤痛,向前看。”她说,“可我觉得,有些伤痛不该被遗忘。它们是我们生命的印记,提醒我们曾如何挣扎,又如何重生。”
“今天,我不只是苏离,也是小星,是我母亲林秀英,是你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名字不同,命运相似。但从此刻起,我们要用自己的声音,写下新的结局。”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几个月后,《反家庭精神控制法》草案被列入立法议程。苏离受邀参与专家咨询组,与法学、心理学、社工领域同仁共同起草条款。她坚持加入一条:“任何以情感胁迫、人格贬损、孤立监控等方式实施的精神控制行为,均构成家庭暴力。”
与此同时,“铃兰之家”扩建新园区,增设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小星主动担任志愿者导师,带领孩子们通过绘画、戏剧、写作表达内心创伤。他的作品《情绪博物馆》在国际儿童艺术展获奖,评委会评价:“这是一个曾被世界噤声的少年,送给所有沉默者的礼物。”
念安也在成长。她在学校发起“倾听计划”,鼓励同学分享家庭困扰。一次班会上,她朗读了自己写的诗:
>“有人说我家很奇怪,
>妈妈曾经消失,爸爸来自远方,
>哥哥不爱说话,外婆从未相见。
>可我觉得,奇怪才是最美的样子。
>因为我们敢哭,敢爱,敢重新开始。”
诗朗诵结束后,全班起立鼓掌。班主任红着眼眶说:“这是我教过最有勇气的一课。”
这一年春天,苏离带着孩子们重返老宅遗址。野生铃兰开得比往年更盛,像是从废墟里挣出的生命宣言。他们在树下种下一棵新苗,挂牌写着:“致所有未曾放弃的母亲”。
返程时,车载广播播放一则新闻:“据最新统计,‘母亲之桥’项目已帮助三百二十七名女性重建生活,其中八十九人成功夺回子女抚养权。该项目模式已被十个城市复制推广。”
季恒转头看她:“你觉得,这就是终点了吗?”
“不。”她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这只是起点。我们要让每个孩子都知道,无论父母犯过错,家庭破碎过,爱依然可以延续。”
夜幕降临时,她再次翻开日记本,在最新一页写道:
>“今天,我终于完成了母亲未竟之事。
>我替她走进法庭,替她说出‘我爱你’,替她证明:一个女人,即使贫穷、病弱、孤独,也有资格做母亲。
>
>这不是胜利,而是偿还。
>偿还给她,也偿还给那个曾经蜷缩在角落、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的小女孩。
>
>我们走了很长的路,穿过谎言、火焰与遗忘。
>但现在,我们可以停下来,轻轻对自己说一句:
>‘辛苦了,欢迎回家。’”
合上日记,她走到窗前。远处城市灯火璀璨,如同星河落地。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小哭包”的新留言:
>“导师,我完成第一个个案了。是个和我当年一样的男孩,他终于肯开口说话了。
>谢谢你教会我:治愈别人之前,先救自己。”
她微笑着回复:**“你做到了,我也做到了。”**
风轻轻吹起窗帘,带来初春的气息。庭院里,那株新种的铃兰在月光下静静舒展叶片,仿佛在等待下一个黎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