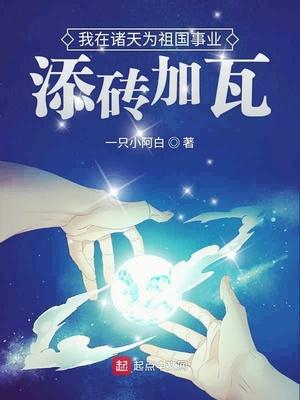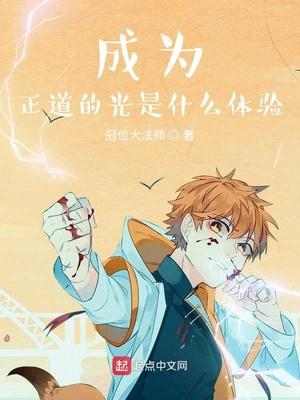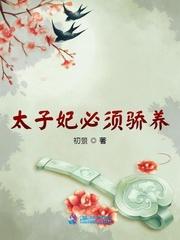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屁股坐正了吗?你就当导演 > 第175章 一拳拳倒一踢踢死彻底碾压(第1页)
第175章 一拳拳倒一踢踢死彻底碾压(第1页)
“开什么玩笑?”
王忠军倒吸一口凉气,心脏砰砰砰的跳,伸手拿过来详细的票房数据报告,眼睛都瞪圆了。
屋子当中,陷入沉默。
“把冯晓刚喊过来,开会。”
王忠军有些麻,连忙吩咐王忠。。。
雪后的北京清晨,空气冷得像刀子。曹忠站在北电老校区门口,看着几个背着摄影机的年轻人从校门里走出来,脚步轻快,眼神发亮。他没有进去,只是默默点燃一支烟,站在那棵已经枯了半边的老槐树下。
他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了。
可他又分明从未离开。
手机震动,是徐正发来的消息:“《人在?途》粗剪完成,72分钟版本,情感节奏都对了。等你审片。”
他回了个“好”,掐灭烟头,转身走向停在路边的黑色红旗轿车。司机老李推门要帮他开车门,被他摆手拦住。“我自己来。”他说,“今天不想坐后排。”
车子驶出胡同时,阳光终于穿透云层,洒在结冰的护城河上,泛起一层碎金般的光。
审片室设在中诚影业地下三层,恒温恒湿,隔音墙厚达八十厘米。曹忠进门时,徐正已经带着剪辑师等在门口。没人说话,只轻轻点头。他们都知道这一刀剪下去意味着什么??不是一部电影的成败,而是一种叙事权力的转移。
灯光暗下,银幕亮起。
镜头从一张火车票特写开始:南京→哈尔滨,硬座,无座补票。画外音是广播站女声机械地播报:“春运期间,客流高峰,请旅客有序乘车……”
接着是三个主角相继登场:黄渤饰演的老李,一个在南方打工十年却始终没混出头的中年男人,拖着破旧行李箱挤上车厢,脸上写满疲惫与麻木;白冰饰演的护士小薇,因母亲病重临时请假返乡,全程沉默地抱着保温饭盒;还有陈明昊演的退伍老兵,在站台上敬最后一个军礼后,独自踏上归途。
没有配乐,只有真实的环境音:列车轰鸣、泡面撕袋声、孩子哭闹、老人咳嗽。镜头冷静得近乎残酷,却又在某个瞬间突然柔软下来??比如老李偷偷把最后一瓶水递给邻座晕车的小女孩,又比如小薇在深夜替一位突发哮喘的乘客做急救时,手指微微发抖。
当画面切到三人被困在暴风雪中的小站,被迫共处一室时,情绪终于爆发。一场关于“家到底是什么”的对话持续了整整八分钟,一句台词都没重复,却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人心最深的痂。
曹忠坐在黑暗中,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一动不动。
直到片尾字幕升起,一首用口琴吹奏的《茉莉花》轻轻响起,他才缓缓闭上眼。
“怎么样?”徐正低声问。
“把那段删掉。”曹忠睁开眼,“就是老兵讲战友牺牲那段,太直白了。观众不是傻子,他们看得懂留白。”
徐正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还有,结尾加一场戏。”曹忠站起身,走到屏幕前,指着最后一帧画面,“现在这个‘你在等’太温柔了。我要更狠一点??让老李到家后,发现房子已经被拆迁队推平了,只剩下一扇门框孤零零立在废墟里。他就站在那儿,手里还拎着给儿子买的玩具飞机。”
房间里静了几秒。
“这……是不是太沉重了?”剪辑师小心翼翼开口。
“现实本来就沉重。”曹忠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我们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让人笑着走出影院,而是为了让那些从来没人拍的人,被人看见。他们的苦,不需要美化;他们的希望,也不需要施舍。我们要做的,是把真实递到观众面前,让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接住。”
徐正深深吸了口气:“我马上安排补拍。”
“别急。”曹忠坐下,点了根新烟,“先送审。”
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的会议室里,气氛比预想的还要凝重。
“这部片子……”一位年长评委推了推眼镜,“基调太灰暗了。尤其是那个拆迁的结尾,容易引发负面联想。”
另一位年轻些的委员反驳:“可这就是现实!多少农民工过年回不去家?多少人千里迢迢赶回来,却发现老家没了?这不是煽情,是记录。”
“记录也要讲究导向。”第一位坚持道,“春节档是合家欢的时候,放这么沉重的东西,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