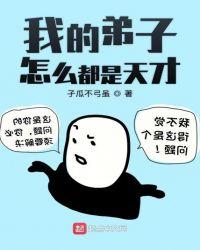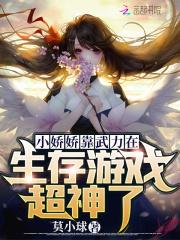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 > 第140章 凤凰儿诞生(第2页)
第140章 凤凰儿诞生(第2页)
“你现在可以听见了。”阿启说,“她们的声音回来了。”
次日,《众声录》上线特别专题:“被删除的母亲”。短短十二小时,涌入超过三十万条相似叙述:有母亲临终前反复念叨“我没教错你”,有祖母在弥留之际突然用几十年未说的方言喊出一个陌生名字,还有人在翻修老屋时,从墙缝中发现一张泛黄纸条:“宝贝,妈妈爱你,别相信他们说的话。”
舆论风暴再起。某主流媒体发文称“过度挖掘私人创伤不利于社会稳定”,随即被网友扒出其主编曾在八十年代担任“清源计划”宣传组成员。公众质问:“你们删掉的名字,够填满几座坟场?”
与此同时,“净忆同盟”发动新一轮反击。他们在短视频平台推出系列短剧《遗忘的美好》,讲述一名青年通过“心灵净化疗程”摆脱“历史焦虑症”,最终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故事。剧情结尾,主角站在高楼俯瞰城市,说出金句:“过去不该是锁链,而应是灰烬。”
讽刺的是,该剧配乐竟是《茉莉花》的变奏版??而这首曲子,正是当年“家庭干预科”用于幼儿催眠的标准音频之一。
阿启没有回应。他带着团队重返云隐洞遗址,在程砚秋提供的卫星热力图指引下,于地下岩层深处探测到异常信号。经爆破开掘,发现一条隐秘通道,尽头是一间未登记的冷冻室。室内存放着数百个密封玻璃舱,编号从A-001至C-327,舱体标签写着统一名称:“静默种子”。
打开其中一个,舱内是一具保存完好的儿童尸体,面部安详,头戴金属环,胸前卡片注明:“赵姓男童,6岁,‘纯净意识移植计划’试验体,状态:休眠失败。”
“这不是冷冻,”法医颤抖着说,“这是**活体封存**。他们想等技术成熟后,把这套‘干净大脑’复制到新人类身上。”
更令人窒息的是,这些孩子的DNA样本与全国失踪儿童数据库比对,匹配率达89%。他们不是孤儿,是被选中的“空白容器”。
消息曝光当日,全国爆发静坐抗议。家长们自发组织“守护童年”行动,在学校门口拉起横幅:“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被净化!”教育部被迫宣布永久禁止任何形式的“认知优化”项目,并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月后。
清明前夕,一位名叫李素珍的老妇人来到传承馆。她拄着拐杖,衣衫朴素,递上一本破旧的工作手册。“我是云隐洞食堂的炊事员,”她说,“那时候,我每天偷偷往孩子们的饭盒里多放一块红薯。”
她翻开手册,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代号与备注:
>A-045:不吃青菜,给他夹肉
>B-112:发烧了,留了姜汤在窗台
>C-203:总哭,唱了《摇篮曲》才睡着
最后一页写着:“有个穿蓝大褂的男人,常来看一个小男孩。他不说名字,只摸他头,走时总掉眼泪。”
阿启浑身一震。“蓝大褂……是我父亲。”
“我知道,”老人点点头,“后来他们把他关进禁闭区,我还偷偷送过饭。他不吃,只反复写一句话。”
“什么话?”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纸片,上面是歪斜却坚定的字迹:
>“阿启,你要活得比我勇敢。”
泪水无声滑落。这是父亲留给他的第二句话。第一句藏在录音里,这一句埋在尘埃中,时隔四十年,终于抵达。
当天夜里,阿启梦见自己走进一间教室。黑板上写着:“今天我们学习‘忘记’这个词。”孩子们齐声朗读:“忘??记??是为了更好的开始。”
他举起手:“老师,如果忘了疼,我们还会保护别人吗?”
全班寂静。
老师摘下眼镜,轻声说:“这个问题……我也问过。”
然后转身,在黑板上补上一行小字:“**但有人记得,就不算真正失去。**”
醒来时,天还未亮。他打开电脑,启动“回声地图”的新功能??“血脉共振”。用户输入亲属姓名后,系统将自动关联其他上传者中是否存在血缘或地理联系。测试运行第一小时,便生成三千余条潜在家族线索。其中一条标注为红色高亮:
>用户【西北牧羊人】上传录音:“爷爷临死前说,他曾在云隐洞看守过一个叫‘萧振邦’的人。”
>关联度提示:该萧振邦,与“神经发育优化工程”负责人同名,但户籍资料显示此人已于1986年病逝。
>进一步比对发现:葬礼照片中的“死者”,实为替身。
阿启盯着那张模糊的黑白照,棺材前跪拜的“家属”中,一人侧脸轮廓分明??正是本该死去的萧振邦。
“他还活着。”周念倒吸一口冷气。
“而且一直躲在体制的影子里。”林昭补充。
他们顺藤摸瓜,追踪到一处位于广西边境的私人疗养院,注册法人名为“陈默”??陈明远曾用名。明显是伪装,但恰好暴露了对方的心理暗示:以受害者之名,行隐藏之实。
程砚秋黑入当地电力系统,调取夜间用电曲线,发现该疗养院地下室存在持续高强度运算负载,远超医疗需求。结合卫星红外成像,确认地下有大型服务器阵列运行,IP地址与多个“遗忘派”网络水军指挥节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