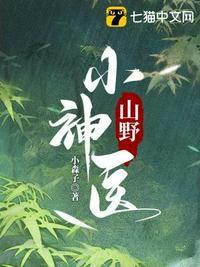笔趣阁>照破山河 > 第 68 章(第3页)
第 68 章(第3页)
然而,杨宴府邸之内,却仿佛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依旧维持着一片静谧安然。杨宴以强硬的姿态,将所有弹劾的奏本和那些污秽不堪的言语都牢牢挡在了门外。
他从未在顾花颜面前提及半分朝堂的纷扰和市井的闲言。
虽然他知晓顾花颜也并不会在意,却还是在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紧紧握住她微凉的手,目光坚定如磐石,对她一字一句:
“外人言语,如过耳秋风,与我无关。我娶的是我心爱之人,非娶他人之口舌。此生能得你为妻,携手白头,于我而言,便是圆满,足矣。”
他们的婚礼,并未因外界的喧嚣和非议而有丝毫从简。杨宴依足古礼,三书六礼,一样不缺,明媒正娶,郑重其事。
虽未广发请帖,大宴宾客,只邀请了少数几位真正知交好友,但仪式本身庄重而温馨,无处不透露着杨宴对她的珍视。
新婚之夜,红烛高燃,跳跃的火焰将新房映照得一片暖融。
顾花颜穿着精心绣制的大红嫁衣,端坐在铺着百子千孙被的床沿,头上覆着象征吉祥的喜帕,耳边能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
沉稳的脚步声渐近,最终停在她面前。一股熟悉的、清冽的气息笼罩下来。接着,喜秤轻轻探入,缓缓挑开了那方隔绝视线的红色锦帕。
视线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是杨宴温柔含笑的眼眸,比平日里更加明亮,仿佛盛满了整个星河。
他亦穿着一身大红吉服,平日里因公务而略显冷硬的面部线条,在温暖烛光的映照下,柔和了许多,俊朗的眉宇间洋溢着无法掩饰的喜悦,令人心折。
“夫人。”他低声唤道,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缱绻与柔情,仿佛这两个字已在心中酝酿了千百遍。
顾花颜脸颊顿时飞上两抹红霞,如同醉人的胭脂。她羞赧地垂下眼眸,长长的睫毛像蝶翼般轻颤,声如蚊蚋,却清晰地回应:“夫君。”
二字出口,一生承诺,一世相依。
————
两人婚后,并未因外界的纷扰而蒙上阴影,反而蜜里调油,恩爱逾常。
而杨宴并非耽于情爱之人,他依旧勤于公务,克尽职守。但回到府中,他不再是那个刻薄肃然的翰林学士,而是顾花颜的夫君。
新婚两月有余,翰林学士杨宴娶“贱籍”女子为妻,并恩爱生子之事,一直都是市井间一桩引人议论的谈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质疑和鄙薄的声音,渐渐被杨宴一如既往的清正官声,以及他们夫妇二人始终如一的鹣鲽情深所淡化。
人们谈起时,语气渐渐从讽刺不解,变成了些许的感叹,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
一年后,在一个玉兰再次盛开的春日,杨府张灯结彩,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顾花颜历经一日一夜的辛苦煎熬,终于平安诞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
产房内,血气未散,顾花颜疲惫却满足地靠在软枕上。
杨宴不顾产房忌讳,紧紧握着她的手,眼底是难以言喻的心疼与激动。他看着嬷嬷怀中那个红彤彤、皱巴巴的小婴儿,目光柔软得能滴出水来。
“辛苦你了,夫人。”他俯身,在她汗湿的额间印下轻柔一吻。
顾花颜摇摇头,目光落在孩子身上,充满了母性的光辉:“夫君,为我们孩子取个名字吧。”
杨宴凝视着孩子良久,又抬眼看向窗外皎洁的玉兰花,沉吟片刻,道:“《诗》云‘君子有徽猷’。徽,美也,善也。之,往也。愿他怀揣美德,行于正道。便叫‘徽之’如何?”
“杨徽之……”顾花颜轻声念着,眼中满是喜爱,“好名字。表字我已想好,便叫‘则玉’吧。”
“则玉。”杨宴几乎是立刻便与她想到一处,问声道:“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望他君子如玉,温润而坚。”
“杨徽之,字则玉……”顾花颜低头,轻轻碰了碰孩子柔嫩的脸颊,柔声道,“我的孩子……愿你德才兼备,温润如玉。”
“……一生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