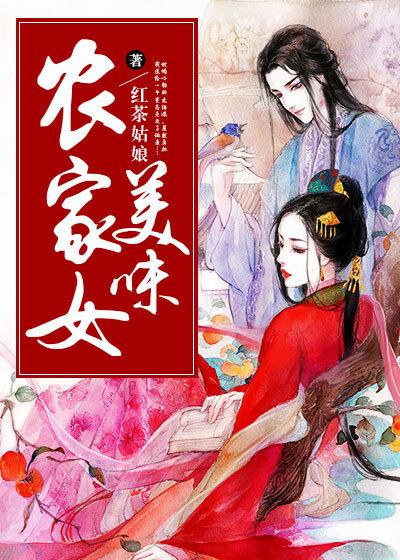笔趣阁>少阁主今天也没有死 > 第39章 窥伺(第3页)
第39章 窥伺(第3页)
挽戈边走,忽然问羊平雅:“羊眙临死前,从国师府出来后,回过羊府吗?”
羊平雅愣了一下,回忆了片刻,才道:“回过。很短……好像只在武堂停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又走了。”
羊平雅依稀记得那日的羊眙。
她也没有想过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哥哥。
为什么会印象这么清晰呢?她想了想,忽然想起来,是味道。
那日羊眙身上带着一种很奇怪的味道,不能说是香气,那味道即使羊平雅身为药王弟子,也完全认不出来那是什么。
所以才会那样深刻。
羊平雅简单把那日奇怪之处讲给了挽戈。
挽戈只嗯了一声:“带我去羊府的武堂。”
武堂就是羊平雅最后一次见到羊眙的地方。
羊府武堂很大很大,里头中心是一整块的青石练场,四面有屋子,遥遥隔着门,也能隐隐能看见密密的铜人和兵器架。
挽戈迈进门,却回头对羊平雅:“你先回去。”
羊平雅迟疑了一下,但是最终道:“好。”
她退了出去。
武堂间这会儿并没有人,只剩下风声。
挽戈独自进了内室。
她并不着急四处翻看,先闭目了几息,耐心感受了一下屋子里的气息。最后才睁眼,径直走向了一个角落。
地面上某一处的砂砾上,武器架和木桩之间,挽戈骤然俯身,指尖从砖缝中拈出一点灰白的粉末,很轻地嗅了一下。
很奇怪的味道。
她眸色一敛。
堂内风声一顿,挽戈抬眼,身形无声一错,整个人影顺着柱子,贴入暗处。
下一刻,哈哈的笑声和杂沓的脚步,从门外闯进来。
“这地方真臭,”那笑声相当熟悉,居然是羊忞,“满屋子的血和汗味,还不如死人香。”
羊忞带了七八个随从。
他还是和先前一样,完全看不出身处诡境之内,一身锦衣,锦履在青砖地面上嗒嗒,毫不避讳。
“二爷,”羊忞身旁的一个随从低声,“人都往后庑去了,堂兄那边还有一堆烂摊子,暂时什么也顾不上。”
“那就好,”羊忞啧了一声,绕着场中木桩转了一圈,像是闲逛一样,“本公子说了,这游戏不好玩吗?让大家都比试起来,拿命来赌,真是刺激过瘾。”
随从谄媚:“二爷雅兴。”
“本公子一向兴致好,”羊忞慢条斯理道,“看着这群蠢货自相残杀,还有我那好堂兄身为羊家少主的废物模样,真有意思,可惜总有不识趣的……”
挽戈藏在立柱后面,呼吸放得很轻。
但是她能感受到,羊忞一行人正不可阻止地要逛到她藏身的地方附近来。
在此时,羊忞的心腹随从却不知道心领神会了些什么:“二爷说的不识趣的,是在说那位萧少阁主吗?她若再动手,局就散了……”
“所以要她别再动手,”羊忞在玩一个扇子,扇骨啪嗒合拢,“或者——再也动不了手。”
另一个随从献策:“听闻那位少阁主先前伤得极重,至今未愈。二爷手上奇物众多,要对付一个强弩之末的病秧子,不过是翻掌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