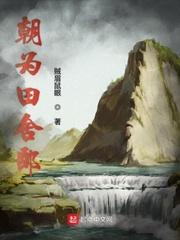笔趣阁>鸢尾下的你 > 羁绊(第1页)
羁绊(第1页)
白露城,维尔纳夫伯爵府邸
书房的光线被厚重的深红色天鹅绒窗帘严密地过滤,只剩下壁炉内跳跃的火焰,在镶嵌着深色木板的墙壁上投下变幻不定、如同幽影般舞动的光芒。空气凝滞,沉甸甸地压着人心,混合着陈旧羊皮卷、昂贵雪茄烟丝以及伯爵怀中波斯猫“雪球”身上淡淡的慵懒气息。
维尔纳夫伯爵深陷在高背扶手椅中,身形依旧保持着军人般的挺拔,但一种被无尽权谋与更深沉思绪磨损后的疲惫感,却从他微蹙的眉心和略显僵硬的坐姿中无声地透出。他修长的手指缓慢而规律地抚摸着雪球柔软的长毛,猫咪纯白的皮毛与他身上昂贵的黑色丝绒家居服形成强烈对比,发出满足的咕噜声,在这片近乎死寂的空间里显得异常清晰。
他的目光并未流连于膝上的爱宠,而是穿透了室内的昏暗,牢牢锁在壁炉上方那幅巨大的肖像画上。
画中的女子极美,拥有与艾米莉亚如出一辙、仿佛凝聚了阳光的金色长发,精心梳理成繁复的发髻,点缀着细碎的珍珠。她的眼眸是比艾米莉亚更为柔和的湛蓝色,如同春日最晴朗的天空,却蕴藏着一丝难以化开的、温柔的哀愁。她穿着维尔纳夫家族标志性的深蓝与银白礼裙,颈项间那枚“凝固的月光”——蓝宝石鸢尾花胸针——熠熠生辉。她是艾米莉亚的母亲,已故的伯爵夫人。
伯爵的眼神复杂难辨。那里面有深沉的追忆,有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承认过的、被时间冰封的情感,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审视与衡量。仿佛在透过这幅美丽的容颜,评估着其背后所代表的联盟、价值与那份沉重的、名为“家族”的枷锁。
笃笃笃。
轻而谨慎的敲门声,像是生怕惊扰了这片凝固的空气。
“进。”伯爵的声音低沉,没有丝毫起伏,如同深潭之水。
书房门被无声地推开,老管家霍金斯端着银质托盘,步履沉稳得像测量过一般走入。他将一杯冒着袅袅热气的红茶轻轻放在伯爵手边的桃花心木小几上,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得像重复了千百次的仪式,带着一种古老的恭敬。
“老爷,”霍金斯的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却依旧保持着绝对的谦卑,“卡西米尔男爵那边,后续的处理已经平息。他对于其私兵越界行为的后果……表示了‘理解’。”老管家的措辞极其谨慎,隐含深意。“他目前的重心,似乎完全放在了搜寻那个失踪的侍女上。”
伯爵端起茶杯,氤氲的热气短暂地柔化了他冷硬的轮廓。他轻呷一口,并未对此发表任何看法,只是极轻地“嗯”了一声,表示知晓。
霍金斯继续汇报,声音压得更低,仿佛怕惊动什么:“至于莫雷尔家族……爱丽丝小姐定期有家信寄回。通过信使往来的路径和一些零散信息推测,她们一行人目前大致是朝着东部边境的丘陵地带移动。速度不快,沿途停留……看起来,更像是一次悠长的游历。”他选用了最中性的词语。
伯爵放下茶杯,杯底与碟子发出轻微却清脆的磕碰声。“游历?”他重复着这个词,语气平淡,却让空气中的压力陡然增了一分,“她倒是寻得了不错的伴游。”他的指尖无意识地在雪球背上停顿了一下,猫咪不满地轻轻“喵”了一声。
他沉默了片刻,那双遗传自古老血脉、显得格外冷冽的眼眸再次投向妻子的肖像,仿佛在与画中人进行一场无声的、无人能懂的对话。莫雷尔家那个小女儿对艾米莉亚超乎寻常的亲近与追随,他怎会毫无察觉。而那个失踪的侍女,卡西米尔私兵的覆灭……他几乎能猜到是谁的手笔。那个银发的狼族少女,以及她麾下那支只听命于艾米莉亚的“小玩具”骑士团,看来依旧忠实地履行着职责。
“霍金斯,”伯爵忽然开口,声音冷硬如铁,“让‘银冕卫’动身。”
老管家霍金斯花白的眉毛几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银冕卫——伯爵麾下最核心、最隐秘的力量之一,直接听命于他,处理那些不便摆在明面上的事务,其地位与作用远超寻常卫队。他们极少出动,每一次出动都意味着伯爵的意志将以最彻底、最雷厉风行的方式得到贯彻。
“是,老爷。请您示下。”
“找到艾米莉亚。”伯爵的声音没有任何温度,“让塞拉菲娜·怀特亲自去。带上我的信。”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丝冰冷到极致的弧度,“去问问我的女儿,这场依靠他人庇护与情感的‘远足’,她打算何时收场。维尔纳夫的血脉,不该沦落到需要依附他人的善意而存活的境地。让她清醒一下,看清所谓‘温度’背后的现实。顺便……”他的目光再次扫过肖像画中妻子温柔的蓝眸,声音里渗入一丝难以捉摸的复杂情绪,“也让我看看,她那份与她母亲截然不同的天真,究竟能让她在这冰冷的世界里走多远。告诉她,逃避毫无意义,现实从不因眼泪而改变。她的母亲……便是最清晰的镜鉴。”最后几个字,他几乎含在唇齿之间,轻得如同叹息,却又重得足以压垮人心。
“明白。我即刻去安排。”霍金斯深深鞠躬,不再多言一字,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书房,轻轻带上了门,仿佛从未出现过。
书房重新被沉寂和壁炉火焰的噼啪声所占据。伯爵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画中人的脸上,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着雪球。那冰冷的蓝宝石眼眸深处,翻涌着无人得见的、深沉的暗流。
东部丘陵地带,无名花海
时间在这片被遗忘的丘陵仿佛陷入了温柔的沼泽。午后的阳光慵懒而慷慨,泼洒在无垠的缓坡上,将大地点燃成一片令人窒息的美景。无数野花——淡紫的鸢尾、金黄的雏菊、洁白的苜蓿、绯红的石竹、湛蓝的勿忘我——以近乎疯狂的姿态绽放着,肆意混合着色彩与香气,织成一张从脚下铺陈至世界尽头的厚重花毯,浓烈的芬芳几乎令人迷醉,暂时洗刷了旅人身上的尘埃与心头的阴霾。
几辆马车在小溪旁投下静谧的剪影,马儿们低头饮水,姿态安然。“银辉守望者”的骑士们在外围如同融入风景的雕塑,保持着警惕的沉默。更远处,无人注意的树荫下或高草丛中,属于帕拉斯骑士团的暗哨如同真正的影子,他们的感知早已与风、与光影融为一体,无声地守护着核心圈的安宁。
营地中心,宁静得仿佛一幅油画。
爱丽丝毫无形象地躺在铺于花丛的厚毯上,一顶软帽盖着脸,雪白的兔耳软软地陷在绒毛里,随着她均匀的呼吸轻轻起伏,彻底被午睡的暖意俘获。阳光在她米白色的发丝上流淌,镀上一层朦胧的光晕。
索菲在临时灶台前忙碌,挽起的袖子露出纤细却有力的小臂。汤锅“咕嘟”地哼唱着,食物的暖香与浓郁的花香交织缠绕,氤氲出令人心安的家的气息。她不时抬眼,温柔的目光掠过众人,最终总是缱绻地落在那个金发的身影上,嘴角噙着一丝心满意足的浅笑。
稍远处,伊莉莎正微微躬身。指尖蘸取的淡绿色药膏散发出清凉醒神的气息,她正将其极其轻柔地涂抹在雅典娜裸露的手臂上。那里有一道深刻的旧疤,像一道苍白而狰狞的闪电,烙印在肌肤之上,诉说着过往的惨烈,也在天气变幻或疲惫时以酸痛固执地宣告它的存在。伊莉莎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专注,红宝石般的眼眸低垂,长而密的睫毛在眼下投下浅浅的阴影,全部心神仿佛都倾注于指尖与疤痕的每一次细微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