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女帝,从招聘诸葛亮开始 > 4050(第13页)
4050(第13页)
夜里,周大石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听着阿翠均匀的呼吸声和老娘时断时续的咳嗽。月光从破窗纸的洞里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个模糊的圆。他想起之前见过的在旱灾中饿死的人,枯瘦的身躯顶着一个大肚子,那是吃土吃的
天没亮他就起来了,阿翠给他塞了块昨晚省下的野
菜团子,硬得像石头。他掰成两半,一半塞回阿翠手里。
“我去报名。”他说。
不管用不用鞭子抽打,他要赚钱,他是个男人他还要养家糊口。
县衙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周大石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有像他这样的庄稼汉,也有城里做小买卖的,甚至还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所有人都眼巴巴地望着县衙那两扇朱红色的大门。
“听说要不少人呢。”王二狗不知何时排到了他身后,“我天没亮就来了。”
日头渐高,县衙的大门终于开了。穿着青色衣袍的姜戈踱步出来,身后跟着两个衙役,一个叫黑夫,另一个则是郑和。
姜戈清了清嗓子,对着排队的人群拱了拱手:
“诸位乡亲,今日登记砖窑招工事宜。还是按照老规矩,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身无残疾者皆可报名。每日工钱八文,中午一顿饱饭。”
不是姜戈对年龄有要求,是砖窑这个活他并不容易干,不是青壮年根本没有力气,而且粉尘飞舞污染严重,对身体又有损伤。
自打姜县令话音落地,人群就骚动起来,像被风吹过的麦浪。
不过百姓刚听见一顿饱饭,不管有工钱没工钱,光是一顿饱饭就够贫苦人家心动了,吃饱多难啊。
“肃静!”黑夫敲了下锣,“招工登记现在开始,一个个来,不许挤!”
队伍中传来轻微的骚动。一个须发花白的老农颤巍巍地问:“大人,小老儿今年五十有二,但身子骨还硬朗,能不能”
姜戈走下台阶,来到老人面前:“老伯,窑上活计太重,您这把年纪”
这窑内高温,粉尘飞舞,对于老人来说这个环境太过恶劣。
“家里孙子饿得直哭啊,”老人浑浊的眼里泛着泪光,“小老儿不怕吃苦”
姜戈沉吟片刻,转头看向郑和。
郑和会意,低声道:“窑场还要几个看管工具的轻省活计。”
“这样吧,”姜戈对老人温言道,“您先登记,到时候我给您安排个照看物件的差事,工钱可能比人家少两文,您看”
老人激动得就要跪下,被姜戈一把扶住:“使不得使不得,您老这边登记。”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郑和执笔记录,遇到不识字的人便耐心询问;黑夫维持秩序,看到抱孩子的妇人就主动让到树荫下等候。
太阳在衙门口那棵老槐树投下斑驳的阴影。
“下一位。”姜戈头也不抬地唤道。
一阵窸窣声后,却没人应答。他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瘦小的妇人牵着个五六岁的男孩站在案前,孩子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小脸脏兮兮的。
“这位娘子”姜戈刚要开口。
“大人行行好,”妇人突然跪下,“民妇林氏,丈夫去年修堤去了没回来听说窑上管饭,能不能”
郑和皱眉:“姜县令,这妇道人家去窑场怕是不便”
砖窑高温,男人大多会光着膀子干活,寡母带着孩子本就不容易,若是被外人的流言蜚语沾染
“民妇什么活都能干!”林氏急急道,“砍柴烧火,洗衣做饭都成!孩子孩子可以放在一旁,绝不耽误干活!”
姜戈看着那孩子瘦得凸出的腕骨,心中一酸。压低声音道:“这样吧,窑场确实不便。我在名册上记下你,到时安排你去厨下帮工,孩子也能跟着吃口热饭。”
到时候把地方隔离开,安排妥当些,也是一个好去处。
林氏眼泪扑簌簌往下掉,拉着孩子就要磕头。姜戈连忙拦住:“快起来,孩子都吓着了。”说着从怀里摸出块糖,蹲下身塞到孩子手里。
轮到周大石时,郑和抬眼温和望着他:“姓名?”
“周大石,周家村的。”
“多大年纪?”
“二十八。”
身子看着也算高大健壮。
只见郑和在簿子上记了几笔,对黑夫点点头。黑夫扔过来一块木牌:“明日来上工,早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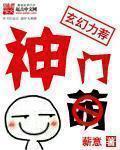
![我成了暴君的彩虹屁精[穿书]](/img/4666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