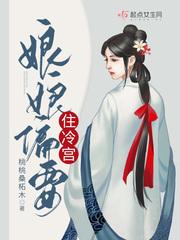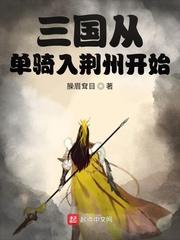笔趣阁>女帝,从招聘诸葛亮开始 > 140150(第6页)
140150(第6页)
“昨夜醉后,忽思太宗皇帝风仪,心向往之……恰与子美相约,若得一见天可风采,便为他赋诗十首。”他语带旷达,“而今竟真至此间,倒是一段奇缘了。”
这么多的历史人物齐聚一堂,是奇缘更是奇景。
“子美昨夜醉意朦胧间曾言,此处可知未来之事?”李白饶有兴致地问道,眼神清澈锐利,哪还有半分醉态。
昨夜杜甫即便醉倒前,也对他的未来三缄其口,越是遮掩,李白心中那簇好奇的火苗便越是旺盛。
毕竟,芸芸众生,谁不想一窥自身命运的轨迹呢?
况且,于李白心中,那“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抱负,如同暗夜中的火焰,从未真正熄灭过。
他看着姜戈,眼神里带着询问和期待。
姜戈犹豫了。她知道历史,知道李白后来的命运——那并非他理想中波澜壮阔的传奇,而是颠沛流离,甚至卷入叛乱风波,晚年潦倒。那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抱负,终究未能实现。
说出来,会不会太残忍?
会不会打碎他此刻眼中的神采?
但她看着李白那双清澈而充满探求欲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丝毫对命运的畏惧,只有一片赤诚和好奇。她忽然觉得,隐瞒或许才是对他的不尊重。
他是李白,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他理应知道,也承受得起。
她深吸一口气,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但依然带着敬意:
“先生……您的一生,会比您诗中写的任何山水都更曲折。”她谨慎地挑选着词汇,“您会见到真正的盛世,也会目睹它的动荡。您会离您追求的寰区大定很近,却又……终究隔着一层无法逾越的纱。”
李白脸上的笑意淡了些,他听得很认真。
姜戈继续道:“您的笔,会写下最辉煌的篇章,也会记录下个人的失意与漂泊。您会拥有世间最极致的洒脱,”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也会尝遍人间最深刻的孤独。”
四周很安静,所有人都听着这段关于未来的判词。
“至于辅弼之愿……”姜戈轻轻摇了摇头,“庙堂之高,终非您的归处。您的天地,在江山万里,在酒杯之中,更在千年之后,每一个读您诗篇的人的心里。您留下的文字,远比任何功业都更不朽。”
她说完了,微微垂下目光,有些不敢看他的反应,她还是不忍心把最后的结局直白的说出来。
沉默了片刻。
忽然,她听到一声轻笑。
抬起头,只见李白仰头喝了一口不知从哪拿出来的酒,眼神清亮,非但没有失落,反而有一种彻悟后的豁达。
“原来如此。”
他笑道,笑容里带着一丝释然,“求之不得,方得自在。庙堂少了一个弄臣,天地间多了一个谪仙。甚好!当浮一大白!”
他又灌了一口酒,衣袖一挥,仿佛将所有烦忧都抛却了。
“既然如此,那更要及时行乐,不负此生了!姜县令,多谢相告!”
短暂的沉默被李白洒脱的笑声打破,他仰头饮尽杯中酒,仿佛将刚刚听闻的未来一饮而尽,化作更浓的诗情。
但空气中仍残留着一丝难以言说的苦涩。
姜戈见状,立刻意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转移话题,缓解这微妙的氛围。她的目光扫过周围这群跨越时空的豪杰,心生一计。
她转向李白,脸上重新露出笑容,还是介绍一下众人。
李白果然被吸引了注意力,他本就好奇这群气度不凡的人物,立刻欣然点头:“妙极!正要结识!”
姜戈侧身,先引向那位始终气度从容、手持羽扇的谋士,声音里带着由衷的敬重:“这位您定然知晓。蜀汉丞相,一生鞠躬尽瘁,星落五丈原的武乡侯——诸葛亮,卧龙先生。”
诸葛亮闻言,唇角含着一抹温雅而睿智的笑意,从容不迫地执扇还礼,声音清朗平和:“亮,见过李居士。”
李白立刻拱手,深深一揖。
面对这位以智慧与忠义名垂千古的贤相,他收起了几分平日里的疏狂,眉宇间流露出的是纯粹的敬仰:“太白不敢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丞相之高风亮节,忠魂义魄,
方是真正令后世千古慨叹,心向往之。今日能跨越时空,得见尊颜,实乃太白三生之幸。”
他的话语诚挚,不仅表达了敬意,更在不经意间,又一次将后世对其的评价带到了当下。
诸葛亮羽扇微顿。
“居士过誉了。”诸葛亮的声音依旧平稳,如静水流深,“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居士诗篇,荡涤人心,流传百世,其功亦不下于庙堂筹谋。能于此间相逢,亦是亮之幸事。”
接着,她指向诸葛亮身旁那位雄姿英发、顾盼间自有风流气度的儒将:“这位是东吴大都督,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火借东风,三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