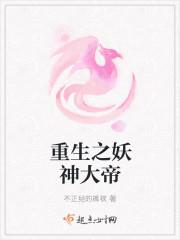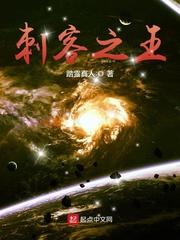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三一二章 状元公(第3页)
第三一二章 状元公(第3页)
五、女子无学,知识断层;
六、庶民子弟,入学受限;
七、官学空转,有名无实;
八、书院垄断,资源集中;
九、体罚盛行,摧残童心;
十、道德虚化,言行不一。
这份报告呈递巡抚后,震动全省。周延儒当场拍案:“此十症,条条见血!若再不改,我辈何颜面对孔孟?”
随即下令成立“清源局”,任命苏录为首席文案,统筹改革方案。同时奏报朝廷,请求特许浙江试行“新式乡学制”:统一教材、定期轮训教师、设立助学基金、开放女子旁听课程、推行德体兼修考评体系。
消息传出,支持者欢呼雀跃,反对者亦蜂拥而起。有御史弹劾周延儒“擅改祖制,蛊惑民心”,更有地方豪绅联名上书,称“苏录一介白身,妄议政令,实乃僭越狂徒”。甚至有人匿名投书巡抚衙门,警告:“小心身边佞人,莫让黄口小儿坏了大事。”
风浪汹涌,苏录却始终沉静如初。他在日记中写道:
>“吾志不在升官发财,而在使每一个愿意读书的孩子,都能坐在明亮的屋子里,捧起一本干净的书。为此纵使千夫所指,万难加身,亦当砥砺前行。”
一日深夜,他伏案修订《通俗劝学歌》初稿,窗外骤然响起急促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干娘披衣立于寒风中,脸色苍白。
“怎么了?”苏录心头一紧。
“胡大厨……昨夜被人打了。”她声音颤抖,“就在回家路上,几个黑影跳出,拳脚相加,说‘再让儿子多管闲事,下次就不只是教训了’……他现在躺在床上,肋骨断了一根……”
苏录浑身一震,拳头紧握,指甲掐入掌心。
但他没有咆哮,也没有立刻奔去医院。他扶干娘坐下,倒了一杯热茶,轻轻揉着她的手背,低声道:“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
干娘摇头,眼中含泪:“孩子,我不怪你。我只是怕……怕你走得太远,回头时,家已不在。”
苏录抬头望向墙上父亲留下的画像,良久,轻声说:“家一直都在。只要我还记得为何出发,家就永远不会消失。”
次日,他照常前往清源局办公,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但在当天的会议中,他首次提出一项新建议:
>“今后所有调查人员,一律匿名行动,资料多重备份,传递使用暗语编码。同时建立‘学童联络网’,由各地聪慧学生传递信息,因其不起眼,反最安全。”
周延儒听完,久久无言,最终叹道:“你终于学会了斗争的艺术??既不失锋芒,又懂得保护自己。”
春去秋来,清源计划逐步推行。第一年,全省重建乡学一百二十三所,培训教师九百余位,发放助学银逾两万两。第二年,首批女子旁听班在杭州、嘉兴开课,三百余名农家女孩第一次拿起毛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而苏录的名字,也渐渐从“解元公”变成了“苏先生”。
人们不再仅仅称颂他的才华,更敬重他的担当。有老儒题诗赞曰:
>“一笔能扛千钧担,寸心可照万里天。
>莫道书生无胆气,敢教乾坤换新篇。”
然而,更大的风暴,正在京城酝酿。
一道来自内阁的密令悄然下达:
“暂停浙江一切教育新政,待朝廷详议后再行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