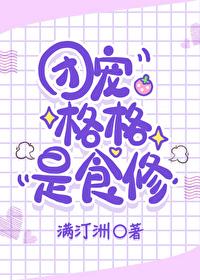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三二二章 苏录的企图(第3页)
第三二二章 苏录的企图(第3页)
礼成之后,天子单独召见。
“你想要什么?”皇帝问。
陈砚之叩首:“臣别无所求,唯愿陛下推行新政:科举考官轮换制、试卷弥封编号双校、设立独立监察院,直隶天子,专查舞弊。并开放言路,允许士子联名上书,监督朝政。”
皇帝沉吟良久,点头:“准。从今往后,每届春闱之前,朕都将亲临国子监,听学子问政。你,便是第一位‘经筵直讲’,位同三品,可随时入宫奏对。”
退出宫门时,阳光普照。
他没有回家,而是走向城南贫民巷。在那里,他创办了一所义学,专收寒门子弟。教室简陋,但墙上挂着一幅大字??“清慎”,乃父亲铜印象形所书。
每日黄昏,他亲自授课。讲至动人处,窗外常有孩童驻足聆听。
某日课毕,一名老妇拄拐而来,颤声问:“您……可是陈大人的儿子?”
“是。”他扶她坐下。
“我是周大勇的母亲。”老人老泪纵横,“我儿临死前说,他要把一封信送到御史台。他说,只要有人肯听,公道就不会死。现在,我信了。”
陈砚之握住她的手,久久无言。
月余后,南方传来捷报:岭南流放官员遗属陆续召回,冤案逐一平反。其中一人,竟是当年失踪的誊录官吴铭??原来他并未溺亡,而是被渔民救起,隐姓埋名三年,如今携完整账册归来。
陈砚之亲赴码头迎接。
两人相见,执手哽咽。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真相了。”吴铭老泪纵横。
“但它一直都在。”陈砚之望着江面朝阳,“只是需要有人愿意点亮它。”
回京途中,他收到一封密信,来自北方边境。边将报告,有蒙古细作试图贿赂兵部郎中,以换取防务图。而那郎中,正是林党漏网之鱼。
他当即上奏,请设“风宪巡察使”,每年巡行各地军政衙门,匿名受理举报,直达天听。
皇帝批复:“所奏皆准。尔后凡陈砚之所荐之人,皆可授监察之权,无需回避。”
从此,朝中多了一个不成文规矩:每逢科举放榜日,新科进士必集体前往陈恪祠前敬香。状元郎则需朗读一篇《清慎赋》,以警自身。
而每当风雨交加之夜,总有人看见一道身影伫立贡院墙外,仰望星空,仿佛在与逝者对话。
他知道,父亲从未离开。
他也知道,这条路没有终点。
但只要灯火不灭,黑暗就永远无法吞噬黎明。
数年后,他辞去官职,游历天下,著书立说。所到之处,皆有学子追随。他的名字不再只是“状元郎”,而是成了“清流之帜”。
临终那日,他躺在江南小院,窗外雨声淅沥。
弟子跪于榻前:“先生可有遗训?”
他微微一笑,只说了四个字:“继续追问。”
而后阖目长眠。
葬礼那天,全国士子罢读一日。国子监门前,三千白幡迎风招展,上书同一句话:
“他曾让我们相信,公道值得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