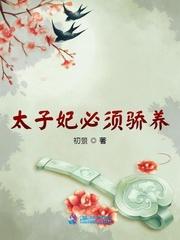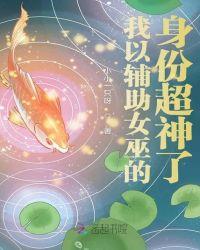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三三一章 新宅(第3页)
第三三一章 新宅(第3页)
他仍住在翰林院南廊那间小屋,每日清晨五更即起,研墨读书,批阅奏章副本,撰写《治平策》十二篇,系统提出整顿吏治、裁撤冗员、改革科举、严惩贪腐、重建监察体系等主张。
有人劝他:“大人如今位高权重,何必自苦如此?”
他答:“我若贪图安逸,便是辜负那些为我而死的人。”
他也开始收徒讲学,不取束?,唯求学生立誓:“终生不说假话,不媚权贵,不欺黎庶。”
其中一名少年弟子问他:“老师不怕再遭陷害吗?”
朱明远望着窗外飘落的桂花,轻声道:“怕。但我更怕闭嘴。一个人沉默一次,就会沉默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变成自己曾经最厌恶的模样。”
岁月流转,五年光阴如白驹过隙。
朱明远的名字已成为朝野清流的象征。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续编》正式刊行,书中直言历代兴衰之因,尤其痛陈“权臣误国、宦官干政、士风堕落”三大痼疾,被誉为“当世镜鉴”。
而当年那位黑袍密议者所言??“十年之后,他自会变成下一个李崇安”??并未应验。
相反,朱明远始终清廉自守,家中无妾,饮食简朴,所得俸禄半数捐予孤寡学堂。每逢灾年,必上疏请减赋税,甚至不惜触怒户部尚书。
某年冬,理宗病重,召朱明远至榻前。
龙床上的皇帝已形销骨立,握着他的手颤声道:“朕老矣……太子仁厚,然柔弱。将来若有奸佞妄图揽权,卿可代朕镇之。”
朱明远伏地泣不成声:“臣只愿江山稳固,百姓安康。至于权柄,从来不敢觊觎。”
理宗叹息:“你这样的人……太少。”
不久后,皇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宋度宗。
新君尊朱明远为“太傅”,参预军国重事,百官敬若神明。
然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度宗登基第二年,北方蒙古大军南侵,襄阳告急。朝廷主战主和之争激烈,宰相贾似道力主议和,愿割江北大片疆土以求苟安。
朱明远在朝堂之上拍案而起:“昔年李崇安私通外敌,诸公群起而攻之;今贾相欲效其故伎,为何默然不语?襄阳乃长江咽喉,失之则江南危矣!宁战死,不屈膝!”
贾似道冷笑:“朱太傅清谈易,临事难。你可知调兵需饷?练卒需时?如今国库空虚,拿什么打仗?”
朱明远当即解下腰间玉带,掷于殿中:“这是我三十年俸禄所积,尽数捐作军资!若有志士,愿随我毁家纾难者,请立于此带之后!”
刹那间,十余名文官脱袍解带,列队而立。
武将张世杰更是拔剑断指,血书“死守襄阳”四字,率三千子弟兵连夜渡江赴援。
民心为之大振,各地豪强纷纷捐粮募勇,终使前线坚守三年,未陷敌手。
而朱明远,也在这一年冬天病倒。
高烧不退,咳嗽带血,御医束手无策。弟子们日夜守护,问他最后有何遗愿。
他虚弱地睁开眼,望向窗外漫天飞雪,喃喃道:“我不求封侯,不求谥号……只盼后世修史之人,能在我的名字下写一句:‘此人生于浊世,未曾低头。’”
七日后,朱明远卒,年五十八。
举国哀悼,百姓自发罢市三日。灵柩出城那日,万人跪送,哭声震野。
多年以后,一位年轻史官在校勘《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三》时,提笔写下:
>“朱明远,字景昭,临安人。少贫力学,母织纱以供读。及长,以直谏显名,历仕三朝,始终如一。虽屡遭构陷,几死者数,然持节不改,砥柱中流。尝曰:‘史官之笔,当如利刃,剖开虚伪,直指人心。纵千万人吾往矣。’观其一生,诚哉斯言。”
窗外春风拂过,纸页轻颤,仿佛回应着那个永不低头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