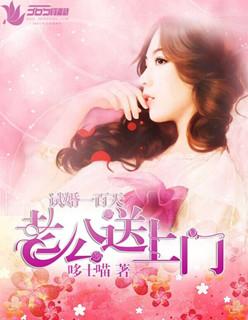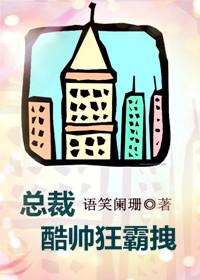笔趣阁>恋爱疗愈手册 > 第124章 生命(第2页)
第124章 生命(第2页)
她瘦得惊人,校服松垮地挂在身上,头发遮住半边脸。值班的周然第一眼看见她时,几乎认不出来这就是那个连续投稿的女孩。但他还是迎上去,笑着递上一杯热可可:
“你是苏晓吧?小满老师说过你会来。她说你最喜欢榛果味,不知道准不准。”
苏晓愣住,眼眶瞬间红了。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最终接过杯子,手指紧紧攥着杯壁,仿佛那是唯一能抓住的温度。
那天下午,林小满带她走进“心语展”的特别录音室。房间很小,四壁贴着吸音棉,中央摆着一支老式麦克风,旁边放着一盏暖黄的小灯。
“这里很安全,”林小满说,“你可以大声哭,可以骂,可以说‘我恨你为什么离开我’,也可以说‘我想你做的红烧肉’。没人会评判你,也没人会打断你。”
苏晓站了很久,终于开口。
“妈……我已经三个月没叫你这个名字了。在家里,我说‘她’;在学校,我假装没事。可是今天,我想好好叫你一次。”
她的声音起初细若游丝,渐渐变得清晰、坚定:
“我好想你。我想你早晨叫我起床的声音,想你下雨天非要塞进我书包的伞,想你每次看我考试成绩不好时不骂我反而给我煮鸡蛋……你总是这样,明明担心得要死,却装作无所谓。”
泪水滚落,她没有擦:“对不起,最后一次吵架是我先摔门的。你说‘早点回来’,我说‘烦死了’。如果我能重来一次,我就抱抱你,说‘知道了,妈妈’。”
录音结束时,整个房间安静得能听见呼吸的起伏。林小满递上纸巾,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握住她的手。
当晚,“未寄出的信”专区多了一条新音频,标题是:《给妈妈的第十九封信》。
播放量在十二小时内突破五千。评论区涌进大量留言:
【我也失去了妈妈。每年清明,我都去坟前读一篇日记。她听不见,但我必须说。】
【我爸走之前最后一句话是“家里米够吗”。到现在我都不敢吃完一整袋米,怕他回来找不到吃的。】
【谢谢你替我们说了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而最令人动容的,是一位匿名用户的回复录音:
“小姑娘,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圈里,一个你不认识的阿姨。她生前最后一条朋友圈是你十岁生日那天,照片是你戴着草帽吃西瓜。她写的是:‘希望我的女孩永远不怕晒黑,因为她心里有光。’她爱你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但一定是拼尽全力的。”
苏晓听完这段录音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想她。原来她的爱,还在别人心里活着。】
一个月后,她开始参加“倾听志愿者”的初级培训。结业那天,她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故事,说到一半哽咽失语。台下没有人催促,所有人都安静等着。直到她抬起头,轻声说:
“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沉默不是唯一的活法。”
项目组为此专门设立了“哀伤陪伴小组”,由经历过丧失的年轻人轮流主持线上沙龙。他们不称其为“治疗”,而叫“共行”??因为我们无法替代谁的悲伤,但可以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
与此同时,陈默完成了一组名为《遗言之外》的插画系列。其中一幅描绘了一个女孩跪坐在墓碑前说话,风吹起她的发丝,而石碑背面,隐约浮现出母亲年轻时的模样,嘴角含笑,仿佛正在倾听。画旁题字:
【死亡带走的是呼吸,
带不走的是牵挂。
而牵挂,是最漫长的告白。】
然而,就在一切看似走向更深的理解与连接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争议席卷网络。
有自媒体发文质疑“心语展”利用他人痛苦博取关注,标题耸动:《谁在消费眼泪?一场打着治愈旗号的情绪生意》。文中截取了几段最揪心的录音片段,指责项目方未经充分授权公开私人情感,甚至暗示存在“情感表演化”倾向。
舆论迅速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这是污名化心理救助;反对者则担忧隐私边界模糊,尤其涉及未成年人时更应谨慎。
林小满召开紧急会议,团队气氛凝重。有人主张强硬回击,有人建议暂时下架敏感内容。
她沉默良久,最终说:“我们不做辩解,只做一件事??公开所有投稿协议、匿名处理流程、危机干预记录,以及每一位参与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然后,请三位投稿者亲自讲述他们的经历。”
三天后,一段纪录片式短片上线。镜头里,苏晓平静地说:“如果我不敢说出妈妈走了我很痛,那这份痛就会杀死我。是你们给了我一个不用伪装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