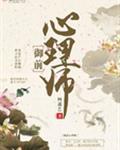笔趣阁>凤谋金台 > 140150(第12页)
140150(第12页)
他抬起头,望向沈承晖,眼神锋利如刃:“圣上也知道。可他试探了无数次,左宰右丞、外戚内史,一个个地查,却始终揪不出其中骨干。为什么?因为你们藏得太好,分散得太彻底,太清楚如何与皇权共处。”
沈承晖没有言语,只是看着王俨,脸色终于有了变化。
王俨继续道:“前太子谋反之案,若真细查,是不是西平集团借圣上之手重塑朝局的一步棋?”
“你们借着圣上的刀除宇文集团,也帮了周王。”
“如今旧案重启,局势突变,朝堂之中风雨欲来,旧案翻起,暗线浮现。”
王俨上身微前倾,语声低沉而清晰:“西平集团作为朝局的平衡器,现在,还不出手吗?”
沈承晖终于说话了。他声音低沉,带着一种穿透寒林的冷意:“王俨,你知道你今日说的话,一旦传出,是足以诛九族的吗?”
王俨坦然答道:“我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说,我们都将被这场乱局吞没。”
他缓缓起身,整了整衣冠:“圣上不是不知道这个集团,只是不知道里面有谁。”
“而我王俨今日,是来传话的,不是圣上的话,是……另一个人的话。”
沈承晖面色微变:“另一个人?”
王俨微微一笑,不言。
但那一笑之后,长厅之内静得几乎连风都止了。
王俨离去时天色已暮,国子监内檐角高挑,鸦影在斜阳下掠过长檐,投下碎碎光影。
沈承晖坐在堂中,良久未动,案前的茶早已冷透,雾气散尽。他面无表情,眼底却沉得仿佛一口古井,风起不起,全看井中是否投石。
片刻后,他伸手从身旁矮几上取过一封帛卷,低头摊开,重新看了一遍王俨方才留下的话语手书。
纸上字迹硬朗有力。
他将帛卷折起,缓缓藏入袖中。起身站定,整了整衣袍,回首看了一眼挂在案后的旧画——那是先帝即位前,太傅赠他的《青松立雪图》,画中苍松傲雪,笔力苍劲,是西平旧人之间往来用印之物。
沈承晖抬手,轻轻抚了画角一瞬,而后转身入了内堂。
片刻后,他亲自点起一支沉香,净手之后,于书案前铺开五张素纸,执笔蘸墨,提气书写,每封信内容不同,但语气皆沉稳老辣,用字极为讲究,几近暗语。
五封信皆写完后,沈承晖未多言,只轻声唤来亲信门生,“鹤三。”
“在。”
“挑最快的马,最稳的人,分五路送出。切记,不许走官驿,不许留信迹,不许出差池。”
“是。”
那门生接过信时,只觉信纸不厚,却如压了千钧,忍不住抬头看沈承晖一眼。
沈承晖却已转身负手,望向远处国子监后园那棵老槐树。
那树下,曾是西平集团旧日议事之地,多少清议之士,多少储君争论、朝局更迭,皆始于一场又一场的密会。
天色微亮,朝阳未起,秦府灯火已明。
秦斯礼立于厅中,手执案卷,身后立着四人,皆是他亲自挑选的办案人手,分属不同系统。
“此次复查旧案,涉及太子谋逆之事,极其敏感。”他目光扫过众人,语声清冷,带着一贯的克制与威严,“你们四人,皆由大理寺、御史台严选调派,不是为我秦某人查案,是为国查冤。若谁心存异意、徇私遮掩……我先斩后奏。”
无人作声,空气如凝霜。片刻后,一名中年御史抱拳:“属下刘彧,谨记职责。”
另一名年轻的大理寺丞亦拱手:“闻案复起,愿尽绵薄。”
秦斯礼点头,又看向自已身后两名亲信:“你二人随我多年,此案由你们统筹卷宗调度。”
他将手中两份令签交出,“三人出外办事,今日先去两处:国史馆史官房,以及大理寺旧案馆。取前太子旧案中,所有当年相关记录。名字、言词、笔供,一一摘录,需在三日内完成。”
两派人马分头行动。
国史馆内,沉静古朴,尘埃浮于晨光。三人中年者敲门入内,年老史官抬眼看他们一眼,道:“又来翻旧案?太子一事,当年圣上亲批,尔等还敢查?”
御史刘彧上前,低声一礼:“是奉秦大人之命,不是质疑圣断,而是重审细节,还原真相。”
老史官冷哼一声,却仍打开木匣,捧出厚重的记录,拂去浮尘,道:“这些年来你们来过几次,每次都问一样的话,却没人敢真动。你们……小心点吧。”
史官之言虽老气横秋,但他们知道,史官房有一物最为关键——日记式记录,非正式档案,是史官亲笔手录,不入正史,亦不进呈朝堂,但往往更贴近真相。
他们翻阅其中,逐字摘录,提取出当年最早提出“谋逆”说法者之姓名——御前供奉刘通。此人曾在先太子左右,而后投向宇文家族。再之后,人间蒸发,官名除籍,极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