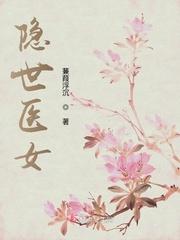笔趣阁>凤谋金台 > 140150(第5页)
140150(第5页)
走一步算一步,是更精明的布局。
秦斯礼收敛心思,回到了眼前。
他转身往厅内走去,也没回头看徐圭言,但默许她跟着自己进来。
于是他径直落座,茶桌两侧铺着细软竹席,两杯茶放在一旁,已凉透。
片刻后,脚步声轻响,徐圭言踏入茶阁,身上的宫装还未换下,披着外衫,显然是刚从宫里赶来,略带风尘。
徐圭言站定,她看见那两杯凉茶,也顿了一瞬,随即心领神会,有人比她来得早。
秦斯礼没应,目光在她身上停留片刻后,微一点头,算作招呼。他不言语,只将指尖在漆黑木几上敲了敲,示意她坐下。
丫鬟们悄然进来,将茶盏撤去,又换上新泡的白毫银针。茶香渐起,清苦清雅,如远山之雾。
气氛凝滞得几乎凝结。徐圭言没有立即落座,而是站在茶几一侧,沉默地看着秦斯礼。她知道,自己今日在这场棋局里,是被逼着落子的一方。
秦斯礼靠坐着,神色平静如水,看似无意,实则以沉默压制对方。他身居高位,话权在手,此时一句话不说,反而更具威压。他在等她先开口。
可徐圭言也没有如他所愿。她只是俯下身,为他斟了一盏新茶。
茶水入盏,细流如丝,茶香散开时,她轻声道:“秦大人请用。”
她的语气并不柔弱,倒是一种避锋藏刃的温和,是朝廷官员用以生存的软甲。此刻,她没有咄咄逼人,没有言辞机锋,反倒示弱一步——不是屈服,而是知进退。
倒了茶,她这才坐下来。
秦斯礼低头看了看那杯新茶,又看向坐在对面的徐圭言。
两盏茶之间,静默仿若时光凝滞。
茶盏中新泡的白毫银针冒出一缕轻烟,香气清苦,穿过檐角徐徐的风,拂过室内两人之间的气氛,清凉,却不柔和。
徐圭言低下头,轻轻摩挲着袖角,像在斟酌什么,又像是在等待时机。
片刻后,她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柔顺得恰如其分,像一尾小舟顺流靠岸:“多谢秦大人那日为我作证,愿提晋王刺杀一事之实。今日得以全身而退,皆赖大人明察秋毫,臣女感激不尽。”
她话语温和,低首敛眉,身姿沉静,一副恭敬而有分寸的臣子姿态。
这不是徐圭言惯常的语调。她擅锋利,但此刻却把自己锋刃尽收,只留下一副中规中矩的模样,仿佛只愿以“下属”之身,与上位者坦然言谈。
这话说得漂亮,动机也不难猜。
然而,秦斯礼只是淡淡地扫了她一眼,没接话,也没接那盏被她亲手斟好的茶。
他将盏盖缓缓一旋,茶汤泛起涟漪。他没喝,动作缓慢得近乎冷淡,仿佛她这一番“谢意”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掀不起他心中半点波澜。
抬眼看向徐圭言,嘴角勾起一点若有若无的弧度,似笑非笑,而摆出一副惯于看破人心的冷漠与疏离。他轻声道:“徐大人误会了。”
他视线掠过那盏茶,也掠过她的脸,寒光落在雕花木窗上,没有一点温度。
“当日我并未为你说好话。”
“只是事情关乎晋王,事关宫闱安危,身为臣子,自应实话实说。那是本分,不是情分。”
这几句话,一字一句都像磐石,不容置疑。
徐圭言神色微敛,垂在身侧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瞬,却没有辩解。
她知道,秦斯礼此时的态度已然说明:他看得出她今日之来不是为一声感谢,而是另有所图。而只要动机不纯,他便绝不肯“公事公办”。
他不接茶,也不接情,更不接受徐圭言的感谢。
秦斯礼缓缓靠坐回椅背,衣袍轻动,姿态如山,目光冷静而高远。他此刻的神情,远不是在看一个同僚,而更像是在看一名请求庇佑的臣属。
——与他两人。
他明知她擅算计,偏
秦斯礼吐出口气,抬手,似漫不经心地抚过案前玉纸镇,又是一笑,那笑却我皆是圣上之臣。”
语气一顿,便听他缓缓而道:
“私下前来,终归不是为了一盏茶,道一声谢。”他望向她,语气平平,却锋芒毕露,“您有何事?”
徐圭言抬起眼,终于与他的视线正面对上。茶香散去,风吹帘动,席间气氛,落入冰雪之间。
她轻吸一口气,收敛起先前的试探与弯绕,终于正视眼前这位高位冷面的大理寺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