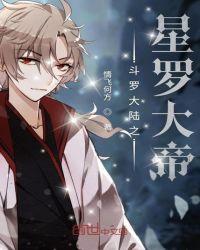笔趣阁>如何拯救德意志 > 第172章 未曾结束(第4页)
第172章 未曾结束(第4页)
更何况,罗马尼亚还掌握著普洛耶什蒂油田,开发时间比美国德克萨斯油田还要早。
若能促使他们加入,或许可以部分弥补奥斯曼倒戈导致的中东石油损失。
“可是,即便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皇帝陛下亲自请求,罗马尼亚至今仍未作出任何回应,他们现在会愿意加入吗?”
“虽然不容易,但並非没有可能。”
罗马尼亚的犹豫,並非因为不愿参战,而是一直在权衡哪一方更具胜算。
而他们在义大利、奥斯曼相继参战,且国內有眾多亲俄派和亲法派的情况下,依旧未向俄法同盟靠拢,足以说明他们认为同盟国並不占优。
『这就够了。』
就这样,在华沙战场上像奴隶一样辛苦工作的可怜汉斯,终於可以暂时喘口气了。
是时候重新以“外交大臣汉斯·冯·乔侯爵”的身份,回归战场了。
。。。。。。
“就这样,终於结束了!”
1913年11月20日。
正当汉斯忙於与罗马尼亚的交涉时,在伊普尔,最后一批英军终於撤离,標誌著这场漫长的逃亡之旅的结束。
但活下来的英军之间並没有爆发欢呼,相反,空气中瀰漫著前所未有的沉重沉默。
他们无法为自己活著离开地狱而高呼庆祝,因为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失去了太多战友。
原本超过三十万的英军,如今存活下来的甚至不到二十万,仅剩约十七万而已。
更糟糕的是,英军採用“战友连”(palsbattalions)或“地区连”的编制模式,让同一个村庄、同一个地区的士兵组成部队。这种编制方式反而让他们感受到的悲痛与衝击倍增。
大多数士兵从小便与同伴朝夕相处,如今却眼睁睁看著熟悉的朋友接连战死。而那些最不幸的人,甚至失去了所有的朋友、邻居,甚至整个连队的同乡,唯独自己孤身存活,陷入无尽的绝望。
“咳咳。。。。。。你是说杰弗里死了?”
“。。。。。。是的,约翰。法国人的炮弹正好落在他接受救治的急救站上。”
在伊普尔死里逃生的托尔金,也未能倖免於这场无尽的悲剧。他的病情已然严重到需要送回本国,但这並不意味著他没有受到损失。
罗布幸运地与托尔金一起逃出了伊普尔,成功存活,但他们的好友,杰弗里·史密斯,却隨著无数大学同学、邻里好友,甚至他们所属的整整一个营,一同在战场上消失。
“哥哥们。。。。。。全都死了?”
“我的儿子们。。。。。。我的孩子们竟然全都战死了,这怎么可能!”
“呜呜呜。。。。。。呜呜呜呜。。。。。。”
当这则噩耗传回英国,全国各地顿时陷入无尽的哀慟之中,失去亲人和挚友的人们的悲鸣迴荡在整个国家。
连一向冷漠寡言的国王乔治五世,也在这一天再也无法抑制悲伤,落下了眼泪。英格兰的大街小巷,隨处可见身穿黑色丧服的哀悼者。
“政府要如何为伊普尔战役的惨败负责?”
“是阿斯奎斯內阁强行下令发动这场无谓的进攻,害死了我们的儿子,他们必须全体辞职!”
隨著时间流逝,悲伤逐渐化为愤怒。
如今,英国人开始寻找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