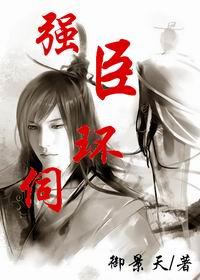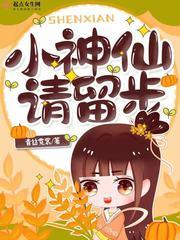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 第121章 合伙人(第1页)
第121章 合伙人(第1页)
杨灿若是当天就带着这群老弱妇孺往丰安庄赶,傍晚前是到不了的。
倒不是这些人会拖他的后腿,这些人几乎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哪怕身子骨已经衰败到明天就要咽气,今天跨上马鞍依旧能坐的稳稳的。
。。。
风自西来,卷过千山万壑,拂过玉门关残破的城楼,穿过黄沙掩埋的隧道,一路向东,直抵南山别院。
那声钟响虽微,却如针尖刺入静夜,惊醒了沉睡的星河。
阿启握紧蝴蝶铃,指节泛白,耳边回荡着方才那一记孤鸣??它不属于守心钟的律动,也不在任何已知共鸣谱系之内。
“不是母钟……也不是初愿钟。”
他低语,目光投向西方天际。
那里云层厚重,仿佛压着一段不肯散去的记忆。
翌日清晨,纸铃坛尚未苏醒,桑皮纸在露水中微微发皱。
阿启已召集陈九娘与三名老书记生于释怀院密议。
他将昨夜所闻复述一遍,并取出随身携带的音纹锁竹简,播放那段来自西域的异响。
声音极细,似风穿石缝,又似骨笛轻颤,频率游走于人类听觉边缘,唯有经特殊调频方可捕捉。
“这不是机械振动。”
一名书记生眉头紧锁,“是……活人的呼吸节奏。”
“还有心跳。”
另一人补充,“每十二拍一次重音,像是某种仪式性诵念。”
陈九娘沉默良久,忽而起身,从箱底翻出一卷尘封已久的西域图志。
她指尖划过羊皮地图上一条隐秘小径:“这条道,叫‘归魂路’。
据敦煌残卷记载,每逢双王血契祭典之年,会有九十九名自愿者沿此路西行,不带干粮,不持兵刃,只背一口空钟,直至玉门关外跪地而亡。
他们的魂魄,会被母钟吸纳,成为镇压记忆洪流的锚点。”
阿启心头一震:“陆知远最后说,‘真正的钥匙不在这里’……难道,所谓契约未解,是指每隔百年,便需有人重走归魂路?”
话音未落,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
一名年轻书记生跌撞而入,手中捧着一封刚由飞鸽传书送达的密报??来自西域边陲驿站“月牙墩”
。
信中写道:**近七日,有七十三名百姓无故离家,皆朝西而去,步履一致,目视前方,口中喃喃‘该还了’三字,如被梦引。
**
“又是睡人?”
陈九娘脸色骤变。
“不。”
阿启摇头,“这次不是被操控……是自发前往。
他们听见了钟声,就像候鸟听见季风。”
他当即下令重启萤火队侦测网络,在全国范围内排查近期异常梦境报告。
结果令人骇然:过去三十天内,共记录到四百一十六例内容高度相似的梦??梦见一座赤红小钟悬于沙海之上,钟下跪满披麻戴孝之人,钟声响起时,所有人齐声高呼:“吾愿代偿!”
“这不是召唤。”
阿启凝视数据板,“是共鸣。
初愿钟净化母钟后,并未切断联系,而是建立了双向通道。
如今,那些深埋心底的愧疚、遗憾、未能尽孝、未能救亲的痛楚,正通过这根无形丝线,反向牵引着人们走向自我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