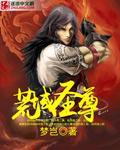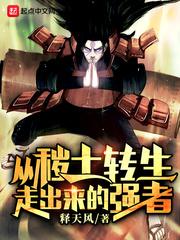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 第129章 风雨初歇云又聚求月票(第6页)
第129章 风雨初歇云又聚求月票(第6页)
剩下的路,他们会自己走。”
梦醒时,东方微明。
阿启披衣起身,走向后院的铃兰丛。
碎埙依旧贴身佩戴,却再无异样。
他知道,它不会再响了。
那些沉睡的灵魂已被唤醒,那些断裂的记忆已被接续,那些被压抑千年的声音,如今在千万个家庭的炉火旁低语、哭泣、歌唱。
他抬头望向远方。
回声塔已不可见,仿佛融入了晨雾。
但就在那一瞬间,他仿佛听见了一声极远极轻的铃响,不是来自天空,也不是来自地底,而是从四面八方传来??从江南的祠堂,从西北的墓园,从东海渔村的船头,从塞北牧民的帐篷……
那是无数人在同时说出一句话:
“我记得你。”
阿启笑了。
他转身走回屋内,取出一张空白竹简,蘸墨提笔,写下四个字:**《草芥录?终章》**。
然后,他一字一句地写道:
>“吾生也贱,如野草生于石缝,如尘埃浮于阳光。
>然吾心不死,因我敢听,敢记,敢言。
>历史非庙堂所独占,记忆非权贵之私产。
>每一个卑微者的呼吸,都是时代的回声。
>故曰:
>**草芥称王,不在权柄,而在不灭之真言。
**”
写罢,他将竹简放入木匣,封存于学堂地窖之中。
他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挖出它。
或许是一个孩子,或许是百年的学者。
那时,他们读到这段文字,不会觉得惊世骇俗,只会轻轻点头,如同确认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几日后,阿启宣布关闭学堂。
不是废弃,而是**转化**。
校舍改作“记忆传承馆”
,藏书不再限于《草芥录》,而是收录全国各地民间整理的口述史、家谱残卷、无名碑拓片。
教师不再固定授课,而是作为“导听者”
,引导访客与自己的记忆对话。
他自己则踏上旅途。
没有随从,没有仪仗,只背着一只旧包袱,里面装着碎埙、竹笔、几件换洗衣物,还有一本空白的册子。
他走遍曾经的“记忆坟场”
,在每一处立下无名碑,碑前放一口小铃。
他拜访年迈的幸存者,记录他们最后一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