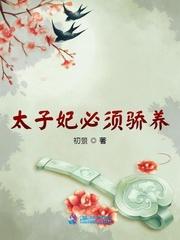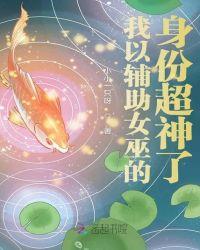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 第138章 朱砂学艺胭脂掉包(第5页)
第138章 朱砂学艺胭脂掉包(第5页)
阿启心头一震。
“意思是你小时候很可能接受过未知剂量的认知调控。
可能是疫苗注射,可能是饮用水添加剂,也可能是幼儿园时期的集体心理辅导课程。
他们不是在等你继承记忆,是在阻止你觉醒。”
电话挂断后,屋内长久寂静。
窗外雪花纷飞,如同无数飘落的纸灰。
阿启望着墙上那幅杜甫诗句的拓片,忽然笑了。
原来他从来不是纯粹的追寻者,而是被设计过的反抗者。
他的愤怒、他的执念、他对记忆的执着,或许早就在某个实验室的预测模型中被计算过。
但他们漏算了一点:即使程序设定了一切,只要还有一个瞬间的动摇,一丝不愿顺从的疼痛,人性就能撕开裂缝。
第二天清晨,他在《众声录》发布新公告:
>“如果你曾梦见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人,请写下他的轮廓。
>如果你家有一本从不打开的旧相册,请拍下第一页。
>如果你听过一句反复出现却不知含义的梦话,请录下来传给我们。
>不必勇敢,不必完整,只要你还记得一点点,我们就还在。”
公告末尾附了一句新增信条:
**“草芥称王,不在战胜多少敌人,而在永不接受被抹去。”
**
春天来临时,第一批“共忆法庭”
巡回展抵达西北小镇。
那里曾是“清源计划”
最大劳改营所在地,如今只剩一片荒原。
当地居民自发清理废墟,在中心竖起一块无字碑,碑下埋着三千二百六十七个未能找回姓名者的骨灰罐。
仪式当天,阳光普照。
一位盲眼老人被孙子牵着手走到碑前,伸手抚摸冰冷石面,喃喃道:
“爸,我带你回家了。”
远处,一群孩子围着一台老式放映机,观看《父亲的最后一首诗》。
画面中,机械钟准时响起,苍老的声音再次吟诵: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风吹过旷野,卷起沙尘,也吹动了插在碑前的一面面小旗。
那些旗帜上没有口号,只有一个个曾经消失、如今重见天日的名字。
阿启站在山坡上,望着这一切,久久未语。
他知道,战争仍在继续。
但他也知道,他们已经开始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