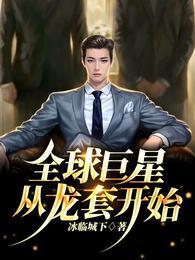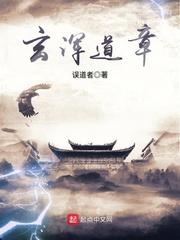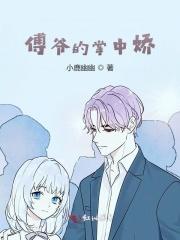笔趣阁>李兆廷综武:我家娘子是状元无弹窗 > 第562章 清场屠龙凶手只有薛青麟(第1页)
第562章 清场屠龙凶手只有薛青麟(第1页)
“假死脱身,死人作案。
这种案情我看过太多太多了。
没有人会怀疑死人,死亡是世上最完美的伪装,尤其是一心求死的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值得恐惧?
没有恐惧,就不会露出破绽。
没。。。
海风在渔村的茅屋外低吟,潮声如息,日夜不绝。
那名青衣男子已在此住了三年零七个月。
他依旧不知自己是谁,却已成了村里最温柔的人。
孩子们放学归来,总爱围着他听故事??尽管他讲的多是些支离破碎的画面:一座桥横跨雾河,石栏上刻着无数名字;一间学堂里,小女孩踮脚挂灯,烛光映着她眼里的星;还有一把油纸伞,在雨中缓缓打开,伞下女子执笔批注,朱砂一点,如血滴落。
他讲这些时,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
每当说到某个片段,胸口便传来一阵钝痛,仿佛有根线被无形的手猛地一扯。
但他从不中断,只是微微皱眉,继续说下去。
孩子们听不懂,却觉得安心,像是听着一首未完成的摇篮曲。
老渔夫曾问他:“你是不是以前教书的先生?”
他摇头,又似点头,“我不知道。
可我总觉得……我答应过谁,要一直醒着。”
“那就醒着。”
老渔夫拍拍他的肩,“活着,就是最大的醒。”
春去秋来,渔村的日子平静如常。
唯有每月十五,男子总会独自出海,在小舟上吹奏那支短笛。
笛声随风飘散,有时引来海鸟盘旋,有时竟让远处礁石发出微弱共鸣。
村中老教书先生悄悄记录下这些现象,写成一封密信,托商船送往江南执灯塾。
信中写道:“疑为‘执灯之音’残响,频率与《醒灯谣》第七变调高度吻合。
吹笛者无师自通,似本能驱动。
建议派遣音律组实地勘测。”
这封信辗转数月,最终落在岭南少年讲师??如今已是执灯塾联合会首席理事??的案头。
他盯着“无师自通”
四字良久,忽然起身,命人备马。
“我要去东海。”
副手惊问:“为何?不过是个渔夫罢了。”
他望向窗外柳枝抽芽,轻声道:“若他是他,那一声笛,便是灯芯将熄前的最后一缕火光。
若不是……也值得走一趟。”
---
与此同时,长安废庙中的三人仍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