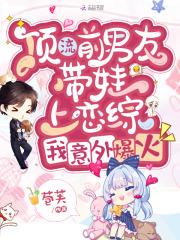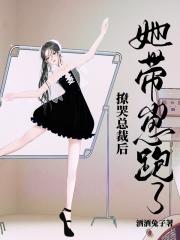笔趣阁>皇修萧舒免费阅读入口 > 第1243章 难缠(第3页)
第1243章 难缠(第3页)
那天之后,陈砚留了下来。
他不做演讲,不写文章,只是每天默默帮我去温室照料幼苗,记录生长数据,偶尔对着某片叶子低声说话。
没人问他讲了什么,也没人追问他的过去。
在这里,故事不必完整,也可以被接纳。
三个月后,全球静语圈传来消息:南极科考站的李昭,在连续七十三天独自守望极光后,于日记本上写下最后一句话??
>**“我终于听见了地球的呼吸。
原来它一直在哭,也一直在笑。”
**
次日清晨,他的帐篷空了,只留下一台老式录音机,循环播放一段无人声的空白磁带。
科学家们检测发现,那段“空白”
其实含有极低频振动,频率恰好与地壳共振波一致。
有人推测,那是他在用自己的心跳,向大地告白。
与此同时,北欧的“空白课”
正式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联合国发布《倾听宪章》修订版,新增一条:
>**“每个孩子都有权利不知道答案,且不必为此羞愧。”
**
而在南美雨林深处,一支原住民部落主动联系静语圈,称他们世代相传的“梦语仪式”
与问树现象高度吻合。
他们邀请引导员前往举行首次跨文明共听仪式。
当夜,三百人围坐火堆旁,轮流讲述梦境。
据说,那一晚,整片森林的植物叶片都发出了微光,动物停止鸣叫,连河流都减缓了流速。
我没能亲临现场,但收到了一段视频。
画面里,一位白发长老手持骨笛,吹出一段无旋律的音符,随后将笛子插入泥土。
几分钟后,附近的藤蔓缓缓缠绕成螺旋状,中心正好对准北极星。
科学家称之为“生物集体意识场”
,而当地人只说一句:
**“树记得所有梦。”
**
这一年冬天特别冷,雪落得厚,压弯了许多树枝。
我在清理积雪时,忽然发现问树主干背面长出一圈奇特的纹路,像是天然雕刻的文字。
我拂去雪屑,借着手电细看,心猛地一沉??
那是林晚的笔迹。
不是投影,不是幻觉,而是树皮自身生长形成的沟壑,恰好拼出一句话:
>**“你种下的不是树,是你愿意相信的世界。”
**
我怔在原地,寒风吹过脸颊,却不觉得冷。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回响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