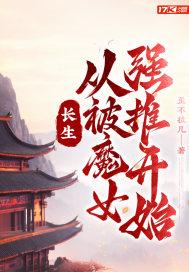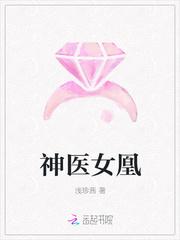笔趣阁>同时穿越:继承万界遗产 > 第171章 我是无敌的(第2页)
第171章 我是无敌的(第2页)
>
>“是你愿意为一句陌生人的哭泣,停下脚步的那一刻。”
影像结束。
林晚怔立原地,泪水无声滑落。
她终于懂了。为什么西伯利亚的语言学家能在雪崩梦境中听见孩子用灭绝语言呼救;为什么火星母亲的布偶能穿越星际出现在地球观测舱;为什么喜马拉雅少年会在昏迷中接过风铃。
这不是科技,是共情的具象化。
是当足够多人愿意“我在听”时,宇宙本身开始回应。
她深吸一口气,打开内部通讯频道,声音平静而坚定:
>“通知所有‘迟来者联盟’站点:第922号信道维持开放。启动‘回声编织计划’第三阶段??允许接收者反向发送回应,无论原寄件人是否存活。”
>
>稍作停顿,她补充道:
>
>“告诉所有人:你可以对过去说话。哪怕对方听不见,也要说。因为听见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未来的你自己。”
命令下达后三小时,第一封“逆向缓递信”成功投递。
发信人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住在北海道海边小镇。他一生未婚,唯一的妹妹在十五岁时溺亡于台风夜。当年警方认定是意外,但他始终怀疑是校园霸凌导致她主动赴死。五十七年来,他从未提起她的名字。
这次,他写下一封信,投入村口新设立的陶制邮筒。信纸用的是妹妹生前最爱的樱花纹笺,墨迹颤抖:
>“阿樱,哥哥错了。
>我不该问你‘为什么不好好活着’。
>你现在疼吗?冷吗?
>如果你还记得我,请让我梦见你一次。
>我想抱抱你,像小时候那样。”
当晚,全球共有十七位曾因亲人离世而自责的人,在梦中见到逝者。他们描述的场景惊人相似:一片开满白色小花的山坡,风铃轻响,有人背对着他们站着,缓缓回头,嘴角含笑,却不说话。
醒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都是写下“我在听”,并注册成为志愿者。
与此同时,土星轨道上的“回音环”空间站监测到一次异常能量波动。数据显示,一段原本属于“未然信件”库的声音突然实体化,并通过量子纠缠通道传回地球??
那是一段对话模拟:
>小女孩(哭腔):“哥哥,那天我不是想死……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的伤口。”
>
>老人(哽咽):“可我没看见……我以为你在闹脾气……”
>
>小女孩:“现在看见了吗?”
>
>老人:“看见了。全是血……全是我装作没看见的血……”
这段声音并未真实发生过,但它如此接近真实,以至于北海道那位老人在收音机里无意听到广播片段时,当场昏厥。
医生抢救时发现,他的左手掌心出现一道陈旧疤痕,本应早已愈合,此刻竟渗出血珠。护士用棉球擦拭时,赫然发现血迹排列成三个微小凸点??盲文的“暖”。
同一天,东京地下城“呐喊广场”遗址的纪念墙前,一名少女献上一束听花。她曾在直播倾诉场中揭露自己被亲父性侵的经历,结果遭到网络暴力,险些自杀。如今她已是心理学研究生,专攻“延迟创伤疗愈”。
她在墙上贴了一张便签:
>“我不再需要所有人立刻听见我。
![真千金有读心术[九零]](/img/220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