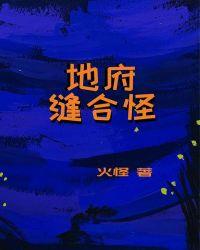笔趣阁>重燃青葱时代李珞应禅溪笔趣阁阅读免费全文 > 第869章 爸刚才是蟑螂(第1页)
第869章 爸刚才是蟑螂(第1页)
面对颜竹笙这样直勾勾的勾引,一般人实在是很难抵挡。
可惜李珞不是一般人。
他抱着颜竹笙柔软的身体,躺在床上却没有下一步行动,只是抚摸着她一头柔顺的长发,随后轻咳一声说道:“今晚不行,下次再。。。
冬至那天,阳光出奇地好。
社区中心的玻璃窗映着暖光,照得“记忆回廊”
里的老照片泛起金边。
袁婉青一早便带着孩子们在展厅里排练“归途之声”
朗诵会??这是“非典型家庭节”
的压轴环节,由十位曾失联或被误解的人朗读自己写给亲人的信,背景音乐是陈默用旧磁带拼接而成的一段城市心跳声:地铁报站、菜场吆喝、医院走廊的脚步、深夜便利店开门的铃响。
王小舟站在角落反复练习,手里攥着那封他改了十七遍的信。
原本只想写一句“奶奶,我织了一双新鞋给你”
,可笔尖一碰纸,眼泪就先落了下来。
最后他写下:“您走之前总说‘小舟要听话’,可我一直没告诉您,那天您昏倒时,是我抱着您哭着喊人……从那以后,我怕极了安静,所以才喜欢织毛线,针尖碰撞的声音,像您还在喘气。”
袁婉青听他试读一遍,没说话,只是轻轻抱了抱他。
她知道,有些话不是为了让人听见,而是为了让自己活下来。
上午十点,林晓阳母亲准时到来,怀里依旧抱着毛线袋。
这几天她已织完三十七双童鞋,每双都绣上不同颜色的名字缩写:有走失孩子的乳名,有服刑少年母亲的生日数字,还有唐果画中那棵槐树的轮廓。
她说:“手慢了,但心还热着。”
赵承志送来一批新的“高墙之声”
录音笔录稿,其中一封来自西北某劳教所的女孩,十五岁,因盗窃超市食物被捕。
“我不是饿,”
她在录音里说,“我是想让监控拍到我,这样我妈就能在新闻里看见我了……她去年走丢了,手机停机,房东说她可能去了南方打工。”
袁婉青立刻联系省际寻亲平台,并将这段音频剪辑成一分钟短片,上传至公益合作账号。
不到半天,转发破十万。
第三天清晨,广西一所养老院护工打来电话:“有个女人天天蹲在门口念一个名字??‘笑笑’,会不会是她?”
他们派阿杰和李锐连夜赶去。
临行前,阿杰把一张存了三年工资的银行卡交给袁婉青:“万一需要押金或者路费,请帮我给她们娘俩用。”
袁婉青看着这张早已不属于问题少年的背影,忽然明白:救赎从来不是一场仪式,而是一次次微小选择的累积。
与此同时,“漂流信箱”
的影响力正悄然扩散。
附近中学的心理老师主动上门,请求设立校园分箱;一位退休邮递员自愿担任每周巡检员,骑着老旧自行车风雨无阻;甚至有外卖骑手组成了“极速响应队”
,承诺三十分钟内送达紧急回信。
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个曾写下“不想死的人”
的少年,如今化名“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