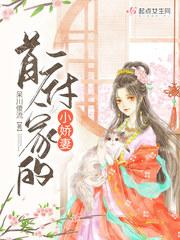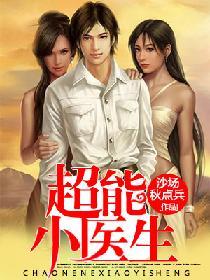笔趣阁>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小说TXT完整版 > 第875章 主人该洗澡啦(第4页)
第875章 主人该洗澡啦(第4页)
项目,组织城市儿童与乡村同龄人结对通信,鼓励他们用手绘插图搭配文字,讲述各自的生活点滴。
首批参与的孩子超过两千名,信件如雪花般飞越山川河流。
然而,并非所有故事都能走向温暖结局。
深秋的一个傍晚,阿杰带回一封匿名信,是从县城边缘一处废弃报刊亭的缝隙中发现的。
信纸泛黄,边缘焦黑,像是从火堆里抢出来的。
内容极其简短:
>“我烧了她所有的照片,可她的影子还在墙上。
我知道我不该活下来,可我又不敢死。
你们说能听见人说话……那能不能告诉我,该怎么忘记一个不该爱的人?”
笔迹紊乱,句尾几乎划破纸背。
团队紧急召开研判会。
根据地理位置和语言特征推测,写信人可能是一名中年男性,极有可能涉及家庭悲剧或情感极端事件。
他们通过技术手段定位附近监控,发现近一个月内,确有一位男子每晚徘徊于该报刊亭周边,行为异常。
正当他们准备联合警方介入时,那人再次出现??这一次,他手里拎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
志愿者伪装成拾荒老人上前搭话,成功取得信任。
男子自称姓周,曾是当地中学语文教师,妻子五年前患抑郁症自杀,遗书中写着“对不起,我再也感受不到阳光”
。
他无法接受现实,一度纵火烧屋,险些丧命。
“火灭了,可我的心没灭。”
他说,“我每天来这里,是因为这是我们当年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她说过,这里的报纸最全,可以剪下诗寄给我。”
他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叠烧了一半的情书草稿,每一封开头都是“亲爱的”
,结尾却空白。
袁婉青决定亲自见他一面。
见面地点选在公园僻静凉亭。
她没穿制服,也没带录音设备,只带了一本诗集。
她翻开北岛的《结局或开始》,轻声念道:“那时我们将动摇但信仰不动那时我们还未相爱但爱情永恒。”
男子浑身一震,眼泪无声滑落。
“你不需要忘记她。”
袁婉青说,“你只是需要学会带着悲伤继续走。
她爱你,所以希望你能活;你爱她,就不该让她成为你生命的终点。”
一周后,周老师主动报名成为“声音档案”
朗读志愿者。
他挑选了五十首关于失落与重生的诗歌,逐篇录制,命名为《灰烬里的光》。
专辑上线当日,评论区涌来大量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