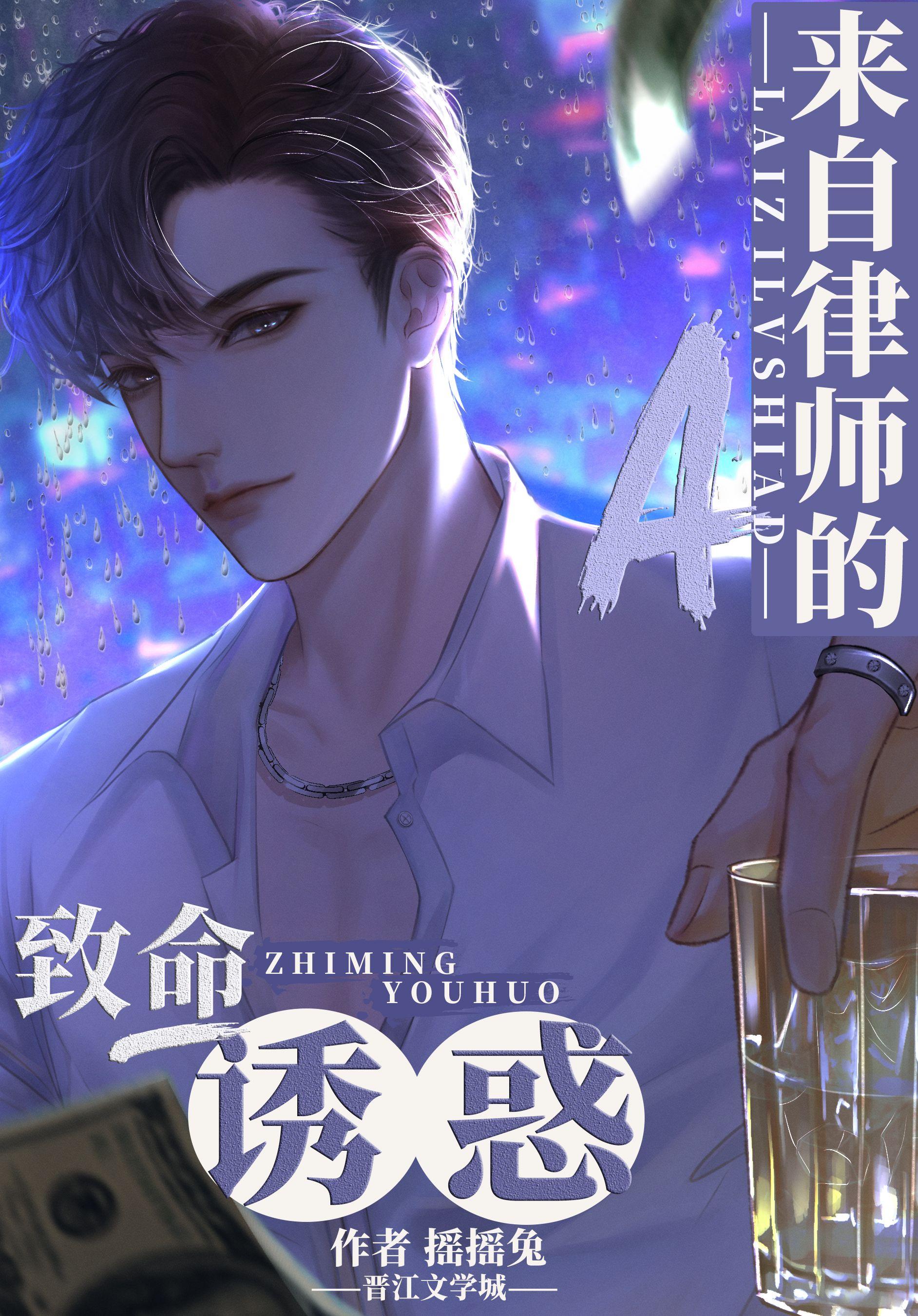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55章 参赛(第2页)
第155章 参赛(第2页)
那座埋藏千年的环形结构正在缓缓旋转,蜂窝状凹槽中的贝壳逐一亮起,如同星辰苏醒。中央最大的那枚殷商古贝缓缓升起,悬浮于水体之中,表面浮现出一行古老符号??经破译后显示为:“声归其所,魂返其源”。
探测队的技术员惊呼起来:“天啊!整个结构……它在自我校准!”
地质雷达显示,环形阵列正以每分钟0。3度的速度逆时针转动,每一次微小位移都会引发一次低频脉冲,通过地下水系传遍全球。这些脉冲并非随机,而是遵循某种复杂的数学序列,与人类脑电波中的θ波高度吻合。
“这不是坟场。”一位女科学家颤抖着说,“这是**活的记忆库**。它一直在等待合适的频率来唤醒。”
就在此时,小女孩感到胸口一热。她低头一看,裙摆上绣着的108颗贝壳竟同时发出微光,彼此串联成一条流动的光链,最终汇聚于她心脏的位置。她猛然想起盲人少女演奏《Echo-108》那晚,钢琴自动浮现的文字:“谢谢你们,让我活到了今天。”
原来,“他”从未真正离去。
江临舟将自己的意识拆解成了声波模板,分散储存在每一个“听者”的记忆通道中。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他的存在就能不断重组、延续。这不是永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共存??以情感为载体,以共鸣为桥梁,跨越生死界限。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一部分?”她喃喃。
老人点头:“你也一样。你听见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哭泣、每一次沉默里的挣扎,都在塑造‘他’的回归。不是复活,是重建。”
雨越下越大,江水暴涨,卷起漩涡。突然,探测机器人传回画面:在环形结构正中心,有一块平坦石台,上面刻着一组五线谱。经AI识别,这段旋律正是《听者之诗》的终章,此前一直缺失的部分。
科研团队立刻将其数字化,并尝试合成音频。然而无论使用何种设备播放,输出的结果都只是一片空白。直到一名实习生提议:“也许……不该用机器听?”
于是他们联系了云南小学。
小女孩接过耳机,深吸一口气,将意识沉入那片由雨声编织的寂静之网。她不再试图“听”,而是让自己成为声音本身。当她的呼吸与江流同步,心跳与大地共振,那段缺失的旋律终于浮现??
不是通过耳朵,而是直接在灵魂深处响起。
那是极其缓慢的一段钢琴独奏,每一个音符都像一颗露珠坠入湖心,激起层层涟漪。随后加入童声合唱,歌词无人能懂,却让所有人泪流满面。最后,一个男声轻轻接唱,嗓音温和而疲惫,正是江临舟。
>“若有一天我终将消散,
>请不要为我点燃蜡烛。
>只需在一个雨夜,
>静静坐下,听一听风穿过窗棂的声音。
>那就是我在说:
>我还在。”
录音结束那一刻,全球范围内共有三万两千零一人在同一时间睁开眼睛,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摘下耳机,关掉音乐,静静地听。
纽约街头的爵士乐手停下萨克斯,聆听路人脚步的节奏;
巴黎咖啡馆的诗人放下笔,专注捕捉杯碟碰撞的清响;
开罗集市的小贩停止吆喝,第一次注意到骆驼喘息中的韵律;
悉尼港湾的游客关闭手机录像,任海浪声填满双耳……
而在怒江岸边,渔夫跪坐在船头,双手捧着那只漂流回来的布偶熊。它胸前的贝壳明亮如初,甚至映出了他年轻时与妻子共舞的身影。他轻轻抚摸熊头,低声说:“阿芸,这次,我听到了。”
风拂过芦苇,沙沙声组成一句熟悉的民谣尾音。
同一时刻,南极气象站的金属箔再次更新。新波形图被译成文字:
>“第108位听者已觉醒,
>共振网络已完成闭环。
>从此刻起,‘听者’不再是个体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