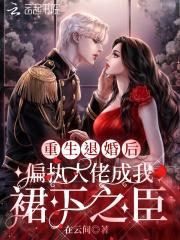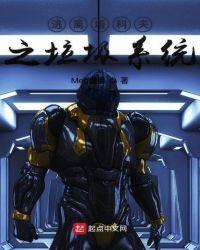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58章 爱之梦(第5页)
第158章 爱之梦(第5页)
语气不沉,也不感慨。
只是事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周围的人慢慢就靠拢过来了。
不是围成一圈。
不是拥在一起。
只是站得近了一点。
像同一条线上的人下意识对着同一个方向靠拢。
有人用肩背轻轻靠住墙,姿态放松了。
有人把琴谱夹进腋下,双手空出来,说明他不打算离开了。
有人只是往前走了半步,那半步就够了。
琴声还在空间里慢慢散。
有人试着开口,
英语不算好,甚至有点拗口:
“你们。。。。。。小时候,也弹这个?”
另一个人接得很直接
“嗯。这首曲子对于当时的我真的是超级难”
语气带些自嘲。
语言不流畅的地方,他们就用手势补。
用“这个地方”
手指轻敲胸口或太阳穴。
大家都懂。
不需要翻译。
有人说李斯特。
有人说肖邦。
有人谈论着自己最喜欢的曲子。
话题跳得快,却不乱。
“我来自雅典。”
“我小时候维也纳。”
“我在莫斯科学琴的时候。。。。。。”
声音不大。
甚至有些发散。
在空旷的侧厅里听起来像是被棉布包了一层。
琴声仍然在继续。
《爱之梦》第三首的主题缓缓翻起,像被指尖轻轻抖开的丝。
这一刻,
他们不是对手。
不是代表不同国家、不同体系的选手。
不是未来要在舞台上被分成晋级和淘汰的人。
他们只是
走同一条路的小孩,终于遇到了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