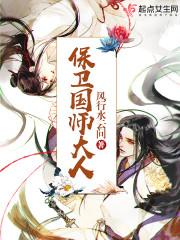笔趣阁>西游之浪浪山的金蟾子 > 第206章 大娃 爷爷你受苦了 吗(第1页)
第206章 大娃 爷爷你受苦了 吗(第1页)
见大娃横空出世,蛋生用自己修行的天书感悟一番,得知了其天生的神通。
正是自己给葫芦爷吃的那颗莲子里的【担山】,以及天罡变化中的【大小如意】。
似乎还有【挟山超海】在里面,但神通的韵味比较淡。。。
阳光如金线般穿过窗棂,洒在学堂斑驳的泥墙上,那八个字??“言路已开,万籁皆声”??仿佛被镀上了一层光晕,熠熠生辉。孩童们围坐一圈,脚边是碎石铺就的地面,头顶是茅草与木梁搭成的屋顶,可他们的眼睛却亮得惊人,像是盛满了整片初晴的天。
那六岁孩子叫小满,他坐在最前排,手里攥着一根削得歪歪扭扭的竹笔,本子上是他刚学会写的三个字:“我、说、话。”他反复描摹着,每一笔都用力极深,仿佛要把这三个字刻进骨子里。
“老师,”他又举手,声音比刚才大了些,“如果我说的话没人听呢?”
先生一怔,抬眼望向这个瘦小的身影。他姓陈,原是南陵府学的一名书吏,因在公文批注中写下“饥民非盗,乃官逼耳”八字,被革职流放至此。他曾以为此生再无执笔之日,却不料在这偏僻山村,竟有孩童愿意听他讲一个“可以问”的世界。
他缓缓起身,走到小满面前,蹲下身来,平视着他清澈的眼。
“从前,”他说,“有个人每天都在井边喊‘我饿了’,可没人听见。不是因为他声音小,而是因为所有人都被教过:别听井里的声音,那是妖言惑众。后来有一天,另一个人路过,蹲下来问:‘你真的饿吗?’那一刻,井底的人哭了。因为他终于知道,自己不是疯子。”
他轻轻拍了拍小满的肩:“只要你还在说,就一定有人会听见。哪怕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就像春天的第一声雷,听不见不代表它没响。”
小满低头看着本子,忽然笑了:“那我也要当那个蹲下来的人。”
窗外,风掠过稻田,掀起层层绿浪。远处山脊上,一座新立的赎言碑正被村民合力竖起,碑上尚未刻字,但已有老者捧着泛黄的手稿,在旁低声诵读。那是一位阵亡老兵的女儿,正将父亲临终前口述的边关真相一笔一划誊抄上去。
而此时,在浪浪山深处,阿篱正独自登上北崖。
她脚步缓慢,却不曾停歇。晨雾缭绕间,她的身影时隐时现,像是一道行走于现实与记忆之间的影子。权杖拄地,发出沉闷的轻响,每一步都似在回应某种遥远的召唤。
裴昭跟在她身后十步之外,没有靠近,也没有离去。他知道,这一段路,她必须一个人走。
崖顶有一块孤石,形如断碑。阿篱走到石前,从怀中取出一枚铜铃??那是林知远生前随身携带的小物,曾在无数个寒夜里为他伴读驱邪。如今铃身已有裂痕,摇动时不再出声。
她将铃放在石上,轻声道:“你说过,只要还有人读书,真相就不会死。现在,他们都开始读了。”
风拂过,铃不动,但她仿佛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回响。
“可我还是怕。”她忽然说,声音很轻,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虚空中的某个影子,“怕这新开的言路,终有一日又被堵上;怕孩子们长大后,又学会闭嘴;怕我们拼尽全力唤醒的世界,最后只换来一阵喧嚣,然后重归寂静。”
裴昭走上前,站到她身旁,望着远方连绵起伏的山脉。
“你也听过那个故事吧?”他问,“关于金蟾子的。”
阿篱点头。
传说千年前,金蟾子游历九州,见世人言语僵化,真话成罪,便吐出体内修炼三百年的“心音珠”,化作初声钟,敲响第一声。此后百年,民间敢言者渐多,朝廷忌惮,遂派兵围剿浪浪山,焚书毁钟。金蟾子临死前留下一句谶语:“吾身可灭,声不可绝。七十二年后,自有执钟人继我志。”
“我们不是第一个执钟的人。”裴昭说,“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每一次言路开启,都会有人想把它关上;每一次真相浮现,都会有新的谎言滋生。但这不是失败的理由,而是继续前行的原因。”
他转身看向阿篱,目光温柔而坚定:“你不必确保永远不黑,只需确保每一次黑暗降临前,都留下一盏灯。”
阿篱闭上眼,许久,终于展颜一笑。
就在此时,天地忽静。
并非无声,而是所有声音骤然清晰起来??风吹树叶的沙沙,溪水撞击岩石的叮咚,百鸟争鸣的啁啾,甚至千里外某户人家锅铲翻炒的声响,全都如潮水般涌入耳中,却又丝毫不乱,层次分明,宛如天籁织成的锦绣长卷。
觉微不知何时已立于崖畔,锡杖点地,口中默念咒文。他胸前那半枚“遗音”铜牌正散发出淡淡青光,与初声钟遥相呼应。
“这是……‘全听境’?”柳芸从林间走出,手中仍抱着那块刻着“李阿牛”的焦木,脸上满是震撼。
觉微点头:“伪声钟覆灭之际,反噬之力撕开了‘听障结界’。从此以后,凡心志纯净、愿听真言者,皆可在特定时刻进入此境??听见万物之声,包括沉默背后的呐喊,微笑底下的悲鸣。”
裴昭闭目感受片刻,忽然睁开眼:“我听见东海渔夫在哭……他们的网里全是死鱼,海水变黑,说是官船倾倒药渣所致,却无人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