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西游之浪浪山的金蟾子 > 第208章 胜率九成八(第2页)
第208章 胜率九成八(第2页)
觉微叹息:“罪者亦是受害者。真正的救赎,不只是惩罚,更是让他们重新找回被剥夺的声音。”
数日后,朝廷颁布新政:凡曾参与压制言论者,若自愿坦白罪行、公开忏悔,并协助还原历史真相,可免死罪,贬为“赎音使”,终身行走民间,记录沉冤。
第一批报名者中,就有那位名叫阿禾的密探。
与此同时,浪浪山声塾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课程。
教室中央摆着一面铜镜,镜面不映人影,只浮现不断流动的文字。这是新研制的“心声镜”??能将人心中最深处的话语具象化,哪怕未曾出口。
十几个孩子围坐四周,有些紧张,有些好奇。
“谁愿意第一个试试?”老师温和地问。
一个小男孩举手,战战兢兢走到镜前。片刻后,镜中浮现一行字:
>“爹打我和娘的时候,我很恨他。但我又怕他死了,我们就没饭吃了。”
教室一片寂静。
老师轻轻抱住他:“你能说出这句话,已经很勇敢了。恨不可耻,害怕也不可耻。重要的是,你现在可以选??要不要告诉村里长老,请他们帮忙调停?”
男孩点头,泪流满面。
接下来,女孩们写下母亲被迫改嫁的委屈,少年们吐露因家贫辍学的不甘,甚至有个残疾孩童写道:“我希望别人看我的眼睛,而不是我的瘸腿。”
每一句话显现,镜面都会轻轻震动,仿佛在回应灵魂的重量。
而在教室外的山坡上,阿篱与裴昭并肩而立。
“你说,我们是不是太过理想?”她忽然问,“总想着唤醒所有人,可有些人宁愿继续睡着。他们觉得梦里的糖比现实的苦好咽。”
裴昭摇头:“可只要有一个孩子因为听见了真相而不再恐惧,我们的路就没走错。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像滴水穿石。今天一个声音,明天十个,后年百万个……终有一天,谎言再也盖不住事实的声响。”
正说着,远处传来马蹄急响。
一名驿使飞奔而至,滚鞍下马,双手呈上一封朱砂封印的文书。
“陛下亲诏!”他喘息道,“南方三十六州联名上奏,请立《言权法》!要求明文规定:百姓有权陈情、有权质疑、有权保留不同意见而不受迫害!并提议设立‘言权日’,每年此日举行全民诵读《守语誓约》仪式!”
阿篱接过诏书,指尖微微发抖。
她想起了那个十二岁少女在紫宸殿上的宣言,想起了矿坑血雨中浮现的三千姓名,想起了今晨村口老妇拉着她的手说:“姑娘,我今天终于敢跟我孙女讲她爹是怎么被打死的了。”
这一切,都不是结束。
她抬头望向初声钟。
月已西斜,晨曦初露。钟体在淡金色的光线中泛着温润光泽,仿佛不再是冰冷的神器,而是一位见证者,一位守护者,一位沉默多年的父亲,终于听见了儿女们的呼唤。
“我们还得走更远。”她说。
裴昭点头:“那就继续走。走到所有人都敢哭、敢怒、敢爱、敢说‘不’的地方。”
当日午时,浪浪山举行大祭。
七十二赎言碑派代表齐聚,携各地新出土的“遗音简”、“冤骨铭”、“密档残卷”,尽数投入初声钟下的熔炉之中。火焰腾起三丈高,燃烧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三百年的压抑与禁忌。
火尽时,炉中流出一泓银液,工匠将其铸成一口新钟,名为“启明”。
此钟无槌,唯以人声共振方可鸣响。且只收真心之语,谎言靠近即锈蚀崩解。
当夜,阿篱再次登上主峰。
她没有带权杖,也没有召唤全听境。她只是静静地站在启明钟前,轻声说道: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还在怕。怕说了会被报复,怕揭了疮疤会流血,怕醒来发现世界比梦境更冷酷。
但请记住,正是因为痛,我们才需要彼此温暖;
正是因为黑暗漫长,我们才更要点亮灯火;
正是因为曾经沉默太久,现在的每一句话,才显得如此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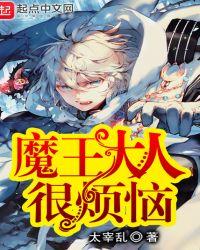

![娇气甜攻总被反派盯上[快穿]](/img/399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