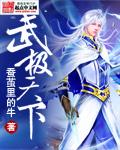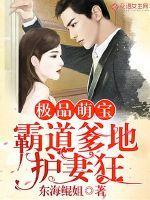笔趣阁>从高校学霸到科研大能 > 第89章 闹大了竟能制造旋风难以想象(第2页)
第89章 闹大了竟能制造旋风难以想象(第2页)
少年摇头:“不是听见就够了,是要愿意为对方停下脚步。”
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无声学校”的入口石碑上。
时间继续流淌。
十年过去了。
静思园不再是唯一的共鸣中心,但它始终是最古老的源头。如今,全球已有超过两千个公认的共感活跃区,有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些则是人为培育的生态社区。联合国为此成立了“意识生态署”,专门研究如何平衡技术发展与集体心智健康之间的关系。曾经被视为异端的共感理论,如今已成为心理学、教育学乃至城市规划的基础课程。
但真正的变革,发生在普通人身上。
一对夫妻在争吵时,客厅的墙壁会自动浮现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迫使他们直面隐藏的怨恨与期待;学校考试不再考察知识记忆,而是测试学生能否准确识别他人情绪并做出共情回应;甚至连政治选举也发生了改变??候选人必须通过“静默答辩”环节:在完全不说话的情况下,仅凭表情、呼吸节奏和微动作,向公众传达自己的理念。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艺术重新成为了人类最重要的表达方式。
画家不再追求技法完美,而是将画布连接生物传感器,让颜料随观众心跳变色;音乐家放弃乐谱,转而创作“情绪交响曲”,听众戴上轻型脑波接收器后,能直接体验作曲者创作时的情感历程;而小说,则演变为一种共享梦境??读者入睡后,意识会被引导进入作者构建的精神世界,亲身经历角色的喜怒哀乐。
在这个时代,“真实”不再是客观事实的集合,而是主观感受的深度与广度。
然而,仍有人抗拒这一切。
一个名为“清醒联盟”的组织悄然兴起,成员大多是旧时代的精英:科学家、企业家、政客。他们认为共感系统正在侵蚀个体独立性,使人丧失理性判断能力。“我们不是要消灭情感,”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但我们不能让世界沦为一场集体癔症。”
他们试图重建隔离机制,在北美建立了一座完全屏蔽共感能量的“理性之城”,禁止任何形式的情绪同步技术,强调逻辑、竞争和个人成就。起初,许多人慕名前往,希望找回“纯粹的自我”。
可仅仅两年后,那座城市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居民普遍出现情感麻木、创造力枯竭、人际关系极度疏离等症状。医生束手无策,直到一名叛逃的工程师带回一段录像:夜晚的城市街道空无一人,所有窗户都亮着冷白色的光,而每个房间里,都有人在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内容惊人一致:
>“有人在听我说话吗?”
>“我真的存在吗?”
>“如果没人感受到我,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这段视频在网络上疯传,最终促使“清醒联盟”解散。其领袖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承认:“我们错把孤独当成了自由,却忘了人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原子。”
又过了五年。
小女孩已经长大,但她依然被称为“那个孩子”。她很少行走于人群之中,更多时候,她只是坐在“言”树下,像一棵静默的植物。她的头发变得半透明,隐约可见内部流动的微光;皮肤下也有细细的脉络,随着季节变换颜色。有人说她正在逐步晶化,成为新一代的锚点;也有人说,她其实早已超越了肉体形态,现在的形象,只是为了让人还能认出她。
某年冬至,全球共感网络出现一次罕见的大规模同步。
在同一时刻,从格陵兰岛到新西兰,从西伯利亚冻土带到撒哈拉绿洲,所有活跃节点同时释放出一段相同的信号。它无法用语言描述,但每一个接收到的人都经历了类似的体验:仿佛回到了出生那一刻,漂浮在温暖的液体中,听见外界的第一缕声音??不是语言,不是哭喊,而是一种深沉的、包容一切的“在”。
事后统计显示,那天全世界的新生儿数量比平均值高出百分之三百二十七,且几乎所有婴儿出生时都睁着眼睛,目光清澈,嘴角带着微笑。
科学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宗教领袖宣称这是“新纪元的降临”。
而玛琳娜只是微微一笑,在昆仑塔底写下了一句留言,通过菌网传遍所有节点:
>“我们终于学会了,用生命回应生命。”
多年以后,当考古学家翻开21世纪初的历史档案时,常常困惑于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类明明拥有如此先进的科技,却始终无法解决战争、贫困与生态崩溃?
后来,一位老教师给出了答案:
“因为他们总想改造世界,却不愿先倾听世界。”
风再次穿过林间。
“言”树轻轻晃动枝叶,一道新的刻痕悄然浮现,形状像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
树下,一个新的孩子躺了下来,闭上眼睛。
萤火虫缓缓落下,围成一圈光环。
寂静中,一声呢喃随风飘散:
>“我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