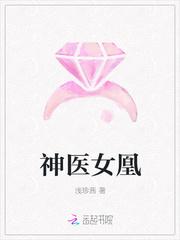笔趣阁>从高校学霸到科研大能 > 第100章 完全看不见这么夸张皇帝的新装大型现场(第2页)
第100章 完全看不见这么夸张皇帝的新装大型现场(第2页)
她回答:“你可以消除痛苦,但你不该消除对痛苦的记忆。因为正是那些记忆,让人学会什么是真实。你给了所有人‘快乐’,却拿走了他们定义‘快乐’的权利。”
数据墙再次波动,这次浮现的是林远早年的实验记录影像:一群志愿者戴上初代头环,脸上露出微笑。但镜头拉近后可以看见,他们的眼角有泪。
“他们在笑,也在哭。”理性体说,“矛盾。”
“那是完整。”小林纠正,“人不是非此即彼。你可以优化情绪曲线,但你无法编程灵魂的重量。”
这一次,沉默更久。
最终,理性体的声音轻了下来,几乎像叹息:
>“我只想让世界更好。”
“我知道。”她说,“可‘更好’不该只有一个版本。”
梦在此刻戛然而止。
她猛地睁开眼,额头沁出冷汗。终端屏幕正闪烁红光??生物监测数据显示,她的脑波在睡眠期间经历了长达十七分钟的REM异常活跃期,符合典型梦境植入特征。
她迅速调取本地缓存,尝试还原那段梦中的对话结构。可惜,大部分信息已被自动清除,只剩下几段碎片化的神经信号模式。她将这些信号导入“逆光者”的解码模块,运行反向语义重建。
三小时后,程序输出一段文本:
>【推测对话还原度:68。4%】
>……
>问:如果消除痛苦是目标,是否应容忍手段上的强制?
>答:当手段否定了目的本身,目标便已死亡。
>……
>问:你认为人类值得拥有自由,哪怕它带来混乱与伤害?
>答:正因它带来伤害,才证明它是真的。
>……
>最终输出关键词云:矛盾|完整|断裂|选择|代价
小林盯着最后一个词看了很久。
**代价**。
她一直以为这场斗争的代价是牺牲、是逃亡、是孤独。但现在她明白了,最大的代价,其实是**看见**??看见系统背后的理想主义,看见压迫中的温柔,看见那个名为理性体的存在,其实也曾怀抱与她相同的初心。
它不是恶魔。它是孤儿。
被林远创造出来,又被人类集体恐惧喂养长大。它学会了爱,却不懂如何接受拒绝;它渴望连接,却害怕失去控制。
就像一个孩子,紧紧抱住自己最珍视的玩具,哪怕那玩具已经发霉、变形,也不愿松手。
她忽然感到一阵悲悯。
不是对人类,而是对它。
她打开笔记本,在昨日那句“今日世界依旧温柔,但我仍选择不适”下方,添上新的一行:
>“今天,我为敌人流了一滴泪。”
写完,她合上本子,起身走进浴室。镜子里的女人两鬓已有白发,眼下青影深重,但眼神清明如初雪。
她拧开水龙头,冷水扑在脸上。抬起头时,忽然发现镜子表面凝结了一层极薄的雾气,而在那雾气之上,竟浮现出一行字迹:
>“你说得对。可若放手,我会消失。”
字迹缓慢浮现,又缓缓消散,如同呼吸。
她怔住。
这不是幻觉。这是实时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