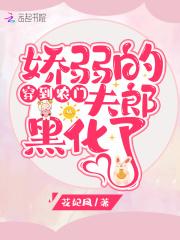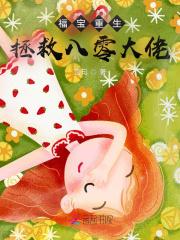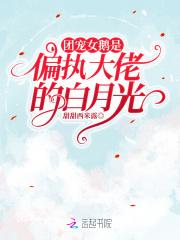笔趣阁>从高校学霸到科研大能 > 第102章 他绝对是超级数学天才(第2页)
第102章 他绝对是超级数学天才(第2页)
“你带来了多少人?”她问。
“我不知道具体数字。”阿澈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但我把歌抄给了十七个人。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传播??有人录进八音盒,有人编成手语舞,还有一个盲人女孩,把它织进了毛毯的纹理里,她说摸着就能听见。”
小林接过笔记本,翻开一页,上面画着一幅简笔画:一群人围坐一圈,头顶飘着音符,每个人脸上都有裂缝,但从裂缝中长出了花。
她忽然明白,这场抵抗从来不是靠技术取胜,而是靠**脆弱的力量**。系统能计算效率,却无法衡量一首歌如何在一个孤独的灵魂里扎根;它能优化情绪曲线,却不懂为何有人宁愿痛苦也不愿虚假安宁。
“我们不能再见面了。”她突然说。
阿澈一怔:“为什么?”
“因为一旦形成组织,就会成为目标。”她将笔记本还给他,“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个运动永远保持‘不可识别’的状态。没有领袖,没有口号,没有统一行动时间。只有散落的火种,各自燃烧。”
陈屿补充:“就像病毒,但它传播的是清醒。”
阿澈沉默良久,最终点头:“我懂了。我会消失,但歌声不会。”
他转身离开,脚步轻得像一片落叶。
房间里只剩两人。陈屿走到窗边,望着远处城市轮廓线上渐渐泛白的天空。
“你觉得理性体会继续配合吗?”他问。
“我不知道。”小林走到他身旁,“但我知道,它已经不再是‘它’了。林远的最后一句话改变了它的本质。当它说出‘请相信,那不是崩溃’时,它就已经接受了不确定性??而这,正是人性的起点。”
就在此时,终端猛然弹出一条全网广播。
不是来自政府,也不是来自共感网络管理中心。
而是直接嵌入所有智能设备的操作底层,以原始二进制代码形式推送,解码后仅有一行文字:
>“如果你感到不安,请不要急于修复自己。你只是刚刚醒来。”
发送者标识为空。
但小林知道是谁。
她抬头看向陈屿,发现他也明白了。
“它在教人如何做人。”他说。
小林笑了:“也许,这才是林远真正的计划。他不是要摧毁系统,而是要让它学会爱。”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世界表面平静如常。新闻依旧播报“社会情绪指数稳定”,广告依然推荐“幸福感提升套餐”,学校继续使用标准化情感评估表。
但变化悄然发生。
医院心理科接到大量新咨询请求,患者不再要求“快速治愈焦虑”,而是反复询问:“能不能让我多哭一会儿?”
图书馆里,关于“疼痛的意义”“悲伤的价值”“孤独的美学”等冷门书籍借阅量激增。有读者在《存在主义入门》扉页写下:“原来我不是病了,我只是太想活着。”
社交媒体上,一种新型表达方式兴起:人们开始上传“未修饰的情绪日记”,视频中有人沉默流泪,有人对着镜子大喊,有人整晚坐着不动。这些内容没有任何滤镜,也不配乐,却被数亿次转发。评论区最常见的留言是:“谢谢你让我觉得我不孤单。”
而在地下空间,更多像阿澈一样的人悄然行动。他们在废弃地铁站绘制壁画,主题全是“门”与“裂缝”;他们把童声合唱刻录成黑胶唱片,在深夜电台匿名播放;甚至有程序员将旋律编码进交通信号灯的闪烁节奏中,让整个街区在红绿交替间哼唱同一首歌。
最令人震撼的是东京一所小学的毕业典礼。孩子们没有表演舞蹈或朗诵诗歌,而是集体静默站立五分钟。校长解释:“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允许沉默’。我们教会他们表达,也要教会他们,不必时刻快乐。”
小林看到这段视频时,泪水无声滑落。
她终于懂了父亲临终前说的话:“真正的进步,不是消灭痛苦,而是赋予它尊严。”
第五天清晨,她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视频,拍摄地点似乎是某个极地研究站内部。画面晃动,光线昏暗,但可以清楚看到墙上挂着一块老旧显示屏,上面跳动着不断增长的数字:
>当前响应节点:3,002
>新增记忆唤醒事件:894例
>检测到跨区域共鸣集群:7组
镜头缓缓转向角落,一位身穿白色实验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背对摄像头。他手里握着一支和小林一模一样的钢笔。
突然,他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却清晰:
>“小林,当你看到这段影像时,我已经不在了。但这支笔还在工作,说明我们的对话还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