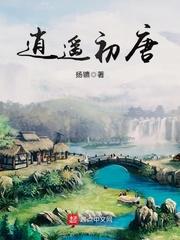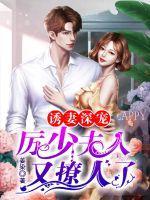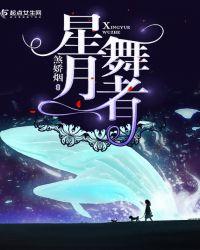笔趣阁>华夏游戏设计师 > 96第 96 章(第1页)
96第 96 章(第1页)
清明过后,樱花落了一地。霍木瑶把那条短信反反复复看了七遍,每一个字都像钉进心里的针,细密而深。她将手机轻轻放在办公桌上,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园区里来往的人群??年轻的程序员背着双肩包匆匆走过,实习生抱着资料在楼道间穿梭,远处食堂飘来饭菜香气,一切如常。可她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程玉华的女儿名叫程晓棠,今年六十八岁,住在杭州郊区的一栋老式居民楼里。她在短信末尾附上了地址和一张照片:黑白合影中,一位穿灰布医袍的年轻女子站在槐树下,眉眼清峻,嘴角含笑,身后是一排低矮的土屋。背面用钢笔写着:“1937年春,沈兰舟医塾毕业留影。程玉华摄。”
霍木瑶当即订了去杭州的高铁票。
出发前夜,她再次调出LUMEN系统中的“程玉华行动”数据图谱。屏幕上,一条由红点串联而成的迁徙路线自北向南蜿蜒延伸:从北平医塾起步,经山西临汾战地医院短暂停留,南下湖南衡阳设立临时救护站,再转至贵州湄潭休整,最后沿滇缅公路深入云南边境。每到一处,都有零星口述记录、残破档案或民间碑文作为佐证。而在1944年初,这条线戛然而止于广西桂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阳朔县高田镇古?村。
据周婉清老人当年手写的零散笔记(经专家辨认整理),医疗队最后一次集体行动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疟疾暴发中。当地村民误以为是“瘴气作祟”,拒绝外人进入,程玉华带领五名队员伪装成采药人潜入村中,连续七天熬药施针,最终控制疫情。但返程途中遭遇日军巡逻队伏击,队伍失散。此后再无确切行踪。
霍木瑶盯着地图上那个小小的红点,指尖微微发颤。她忽然意识到,这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追索,更是一个女儿对母亲跨越八十年的呼唤。
次日清晨抵达杭州时,天空正下着细雨。程晓棠已在小区门口等候。她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藏青色外套,手里撑着一把旧伞。见到霍木瑶,她没有多言,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转身带路。
屋子很小,约莫四十平米,一室一厅加厨房卫生间挤在一起。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结婚照:程玉华与丈夫陈志远并肩而立,两人皆着中山装,神情庄重。照片下方摆着一个木框,里面嵌着一枚褪色的徽章和半截烧焦的笔记本边角。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程晓棠低声说,“他说,母亲走的时候,只带走了药箱和这本笔记。后来家里遭过一次火灾,大部分都毁了……但这一页,他拼了很久才补全。”
霍木瑶接过那页残片,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一段话:
>“今日抵桂北,疫势未歇。我决意率队入村。若三日后无讯,请诸位自行撤离,勿再寻我。生死有命,仁心无悔。??玉华三十三年四月初二”
字迹潦草却坚定,墨水已被烟熏得泛黄。霍木瑶喉咙一紧,几乎说不出话。
“我妈……从来不是什么大人物。”程晓棠坐在床沿,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她原本可以在北平当教授,可偏偏要去乡下教女娃学医。我爸说,她总觉得自己欠这个国家什么,非得还完不可。”
她顿了顿,望向窗外的雨帘:“我出生那天,她在前线。等她回来,我已经两岁了。她抱我的时候,手还在抖,说是刚做完一台手术,没来得及洗手。”
霍木瑶轻声问:“您恨过她吗?为了别人,丢下你们。”
程晓棠摇头:“我不恨。我只是……想知道她最后去了哪里。我爸临走前交代我,如果有一天能找到她的消息,一定要替他说一句‘我一直在等你回家’。”
那一晚,霍木瑶留在了程家。她们翻出了更多旧物:一封未寄出的家书草稿、几张模糊的集体照、一本手抄的《伤寒论》注解。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张1944年的《西南日报》剪报,标题为《巾帼赴难:女子救护队血染桂岭》,文中提及一支由皖南女子程姓医生率领的民间医疗队,在阳朔一带失踪,疑遭敌军杀害,全文仅三百余字,未列名单。
“我们不能再让这段历史只剩三百字。”霍木瑶握紧剪报,语气坚决,“我们要让她重新活一次,以真实的名字,真实的面容,真实的足迹。”
回到北京后,她立即重启“程玉华行动”第二阶段,目标直指古?村。这一次,不再只是收集证据,而是要实地重建那段最后的日子。
项目组再度集结,新增两名人类学博士与一位战地医学史专家。他们联系了广西地方志办、桂林博物馆及当地村民协会,多方协调后,终于获准进入古?村进行田野调查。
五月的桂北山野绿得浓烈,溪水潺潺穿村而过。村子依山而建,石板路湿滑,两侧是斑驳的老屋。许多人家门楣上仍贴着“驱疫符”,据说早年瘟疫频发,村民信巫不信医,直到那支女子医疗队来了。
他们在村祠堂找到了一位九十一岁的覃阿公。老人耳聪目明,一听“程医生”三字,立刻从柜子里取出一只陶罐,倒出几包早已干枯的草药。
“这是她们配的‘退热散’。”他指着其中一种紫茎小草说,“那时候村里死了十几个孩子,都是高烧不退。她们来了,不分昼夜熬药,还教我们怎么识别药材。有个小姑娘,每天蹲在溪边洗绷带,手泡得发白开裂也不停。”
“您还记得程队长的模样吗?”霍木瑶小心翼翼地问。
覃阿公闭上眼,缓缓描述:“瘦,很高,说话轻,但很有劲。左耳缺了个小角,说是早年做手术被玻璃划伤的。她最爱穿一件灰布褂子,袖口磨破了也不换。”
霍木瑶心头一震??这与杨阿婆提供的铜牌背面刻痕完全吻合!她立刻调出数据库比对,发现全国仅有三人曾记录过程玉华“左耳残缺”的特征,且时间地点一致。
更重要的是,覃阿公提到,医疗队离开前夜,曾在村后山腰搭起临时帐篷,彻夜开会。“她们说,接下来要去湖南接应一批伤员,必须绕开日军哨卡。走之前,程队长把我叫去,托我保管一样东西。”
他颤巍巍地领众人来到一座荒废的柴房,在墙角挖出一个锈铁盒。打开后,里面是一本完整的日记、三封未寄出的信,以及一张手绘地图。
日记最后一页写道:
>“四月初五,晴。昨夜梦见晓棠,她喊我‘妈妈’,声音很清亮。我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我不能退。若我死,望有人知我为何而死;若我生,必归家园。此心昭昭,如月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