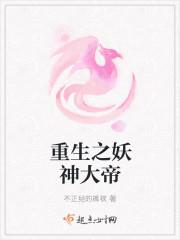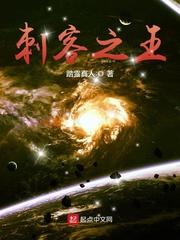笔趣阁>本王的科技树长歪了 > 火器的禁忌(第2页)
火器的禁忌(第2页)
赵楷不断改进设计,调整石灰与水的比例、容器的结构和强度。他甚至异想天开地尝试加入硫磺、磷粉(极危险!)等助燃物,但很快放弃,太容易失控。
最终,他做出了一种相对“可靠”的石灰发热弹。其威力远不如火药爆炸弹,但能在小范围内产生持续高温,对付木质结构或人员有一定效果,且制造相对简单,原料易得。
他将样品和测试结果谨慎地报送给曹玮和军器监。
军器监的官员看了,面面相觑,表情古怪。这东西……说它是火器吧,它没用药;说它不是吧,它又能放火……算是个奇门玩意儿。威力嘛,聊胜于无。
曹玮倒是觉得有点意思,至少是一种新思路,且相对“安全”,便批准小批量试制,送往前线试用。
前线反馈回来:效果……十分尴尬。有时能点燃一些茅草木头,有时就是个哑弹(隔板没碎),有时石灰粉喷出来,呛得自己人眼泪直流……被边军戏称为“嗞哇乱叫弹”或“白烟障眼弹”,实用性很低。
赵楷得知后,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这已经是他能在“稳妥”框架下做到的极限了。
砲弹研发再次陷入僵局。
然而,赵楷这些“不务正业”的尝试,虽然军事价值有限,却意外地带来了一些副产品。
为了制作石灰弹,他需要密封性更好的容器。这促使他改进了陶罐的烧制工艺,尝试了不同的粘土配方和釉料,无意中提升将作监的陶瓷制作水平。
为了测试弹体强度,他改进了落锤冲击试验装置,积累了一些材料冲击性能的原始数据。
甚至那失败的“水泥弹”尝试,也让他对胶凝材料有了一点点粗浅的认识。
这些微不足道的“歪楼”成果,暂时看不到任何实用价值,却如同散落的珍珠,埋藏在了科技树的土壤里。
就在赵楷为砲弹焦头烂额、深感前途无亮之时,一个来自遥远南方的战报,却以一种谁也未曾料到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局势,也暂时将他从砲弹的泥潭中解脱了出来。
战报不是来自西北,而是来自广南西路(广西)!
广源州(今广西西南部及越南部分)蛮酋侬智高反叛!率众攻陷邕州(南宁),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一路攻城略地,兵锋直指岭南重镇广州!岭南震动!
侬智高军队骁勇善战,尤其擅长山地丛林作战,宋军屡战不利,损失惨重!
消息传至汴京,朝野哗然!朝廷的注意力瞬间从西北边境,转移到了南方平叛上!
枢密院紧急调兵遣将,任命狄青为宣抚使,率精锐禁军南下平叛!
狄青要出征了!
赵楷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一震。狄青出征,意味着狄明月……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狄青在出征前,特意向枢密院和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提到了赵楷!
奏疏中,狄青盛赞“靖虏弩”和“骑兵弩”于山地丛林近战中之效,请求调拨一批新式弩机随军。同时,他特别指出,侬军多据险寨,攻坚需利器,闻将作监有“镇远砲”,虽笨重,然或可于关键之战中发挥奇效,请旨酌拨数架,并派熟知砲械之工匠随军保障。
皇帝准奏。
于是,一道新的命令下达至将作监:紧急生产一批靖虏弩、骑兵弩,并抽调三架“镇远砲”及配套砲弹,选派得力工匠,随狄青大军南下平叛!
赵楷的差事,瞬间从“研制新砲弹”变成了“保障现有装备”!砲弹的压力暂时解除!
他长舒一口气,立刻全力投入到装备生产和调配中。这是实实在在的军务,不容有失。
他亲自监督弩机和砲械的检验、包装和装车。选派工匠时,他犹豫再三,最终决定让鲁小鱼带队前往。鲁小鱼手艺精湛,对弩机和砲械结构最熟悉,且年轻机灵,能吃苦。
“小鱼,此去岭南,山高路远,瘴疠横行,战事凶险,一切小心!”赵楷郑重叮嘱,“务必保障砲弩完好,但更要保全自身!遇事多问军中匠师,不可逞强!”
鲁小鱼既紧张又兴奋,用力点头:“先生放心!小鱼定不辱命!”
狄明月得知父亲要出征,鲁小鱼也要去,吵着闹着也要跟去,被狄青严厉喝止。
大军开拔之日,汴京城外,旌旗招展,甲胄鲜明。狄青顶盔贯甲,面具下的眼神锐利如鹰。赵楷站在送行的官员队列中,看着鲁小鱼等人随着辎重车队远去,心中默默祈祷。
他不知道,这支南下的军队,以及那几架笨重的“镇远砲”,将会在遥远的岭南,上演怎样的一幕。而他那些“歪打正着”弄出来的器械,又将在真正的战场上,经历怎样的考验。
科技的树苗,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又将迎来新的未知。